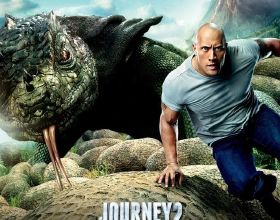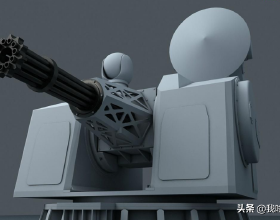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西方知識分子都在追逐海神和美人魚。沃恩·斯克里布納跟蹤報道了這次狩獵,揭示了人類假定的水生祖先是如何成為神奇的螢幕,在上面投射地理、種族和分類差異的理論。
1736年5月6日,博學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他的《賓夕法尼亞公報》上告訴讀者,最近在百慕大發現了一隻“海怪”,“它的上半身形狀和一個12歲的男孩一樣大,留著黑色的長髮;下半部分像一條魚。”顯然,這種生物的“人類形象”激發了他的捕獲者讓它活下來。1769年的《普羅維登斯公報》也有類似報道稱,在法國佈雷斯特海岸附近,一艘英國船隻的船員看到“一個像男人一樣的海怪”繞著他們的船盤旋,有一段時間還看到了“船頭上一個代表美麗女人的身影”。船長、駕駛員和“全體船員,包括二、三十人”證實了這個說法。
上面的例子很能代表早期現代英國人在報紙上看到的東西。這些相互作用的報道告訴了我們很多。像本傑明·富蘭克林這樣的聰明人認為這樣的遭遇是合理的,他們花時間和金錢在他們廣泛閱讀的報紙上刊登。透過這樣做,出版商和作者幫助維持了對這些奇妙生物的好奇心。當一個倫敦人拿著報紙坐下來(也許就在名字很貼切的美人魚酒館裡),讀到又一個美人魚或海神目擊的例子時,他的懷疑可能會轉化為好奇。
這一時期哲學家們對美人魚和海神的爭論表明,他們願意在更大的探索中擁抱奇蹟,以理解人類的起源。自然學家使用了廣泛的方法來批判性地研究這些奇怪的混血兒,進而斷言人魚的存在是人類水生起源的證據。正如他們在全球旅行中遇到的其他生物一樣,歐洲哲學家利用各種理論——包括種族、生物學、分類學和地理差異——來理解人魚以及人類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
西方人的好奇心和帝國擴張的結合,很好地體現在人魚的文化關聯性上。富有的個人和哲學社會資助博物學家、植物學家和製圖師對新世界的探險,希望他們可以拓寬人類對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們在世界中的地位。在對美人魚和海神越來越多的調查中,博物學家表現出了對奇妙事物越來越大的興趣。重要的是,它們還揭示了過去兩百年來科學研究過程的巨大變化。18世紀的博物學家沒有嚴格依賴古代文獻和傳聞,而是聚集了各種“現代”資源——全球通訊網路、博學的出版機會、跨大西洋旅行、標本程式和學術團體——來理性地研究許多人認為是幻想的東西。因此,越來越多的紳士既堅持也避免了所謂的開明邏輯的敘述,他們將眾所周知的、有效的研究方法應用到神秘的人魚身上。這樣一來,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柯頓·馬瑟、彼得·柯林森、塞繆爾·法爾斯、卡爾·林奈和漢斯·斯隆就把我們和同時代的人對科學、自然和人類的概念複雜化了。簡而言之,西方世界最聰明的人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世界各地追逐人魚。
倫敦皇家學會證明了這一努力的關鍵,它既是合法科學調查的寶庫,也是生產者。羅伯特·西伯德爵士,一位受人尊敬的蘇格蘭醫生和地理學家,非常理解學會對突破性研究的渴望。1703年11月29日,他寫信給協會的總統漢斯·斯隆爵士,告訴這位倫敦先生,西博爾德和他的同事正在記錄一份關於蘇格蘭兩棲動物的記錄,並附上了銅版影象,他希望將這些影象獻給皇家學會。意識到學會對最新研究的興趣,西博爾德告訴斯隆,他“添加了一些描述和一些兩棲水生動物的數字,以及一些混合種類,就像美人魚或塞壬有時在我們的海洋中看到的。這裡有兩位十八世紀的主要思想家,他們就人魚問題交換了博學的見解。
1716年7月5日,科頓·馬瑟也給倫敦皇家學會寫了一封信。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位波士頓博物學家經常詳細描述他的科學發現。然而這封信的題目有點奇怪——標題是“海神”,這封信顯示了馬瑟對人魚存在的真誠信仰。這位倫敦皇家學會的研究員開始解釋說,直到最近,他還認為人魚並不比“半人馬或斯芬克斯”更真實。馬瑟發現了無數關於人魚的歷史記載,然而,馬瑟指出,由於“普林尼派在我們那個時代名聲不太好”,他把這些古老的說法大多都說成是假的。當馬瑟讀到博愛斯圖和貝隆尼斯等受人尊敬的歐洲思想家的各種古代記載時,他對這種生物存在的“懷疑”“得到了更多的力量”。
然而,馬瑟並沒有完全信服,至少在1716年2月22日,當“三個誠實可信的人,乘船從米爾福德到佈雷福德(康涅狄格州)”,遇到了海同。聽到這個第一手的訊息後,馬瑟只能驚呼:“現在我終於完全克服了輕信,我現在不得不相信神的存在。”當怪物逃跑時,“他們看得很清楚,看到了他的頭、臉、脖子、肩膀、胳膊、胳膊肘、胸部和背部,全都是人形……下部是魚的,顏色像鯖魚。”雖然這個“海神”逃脫了,但它讓馬瑟相信了人魚的存在。馬瑟堅稱他的故事不是假的,並向皇家學會承諾,他將繼續傳播“所有自然的新事件”。
著名的博物學家卡爾·林奈也投身於研究美人魚和海神。林奈在報紙上讀到有關在瑞典Nyköping看到美人魚的詳細報道後,於1749年寫信給瑞典科學院,敦促進行一次狩獵活動,“活捉這種動物或將其精神儲存下來”。林奈承認:“關於美人魚的存在是事實,還是一些海洋魚類的傳說或想象,科學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但在他看來,這種罕見現象的發現“可能會導致該學院可能實現的最大發現之一,全世界都應該感謝該學院”,因此回報大於風險。也許這些生物可以揭示人類的起源?對林奈來說,這個古老的謎團必須被解開。林奈以其對分類學的貢獻而聞名於世。
荷蘭藝術家塞繆爾·法洛爾也聲稱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發現了人魚,這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爭論,爭論跨越了各大洲和各種媒體型別。從1706年到1712年,法洛爾住在印度尼西亞安汶,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擔任神職人員助理。在福洛爾斯在“香料島”任職期間,他畫了各種本地動植物的圖例。其中一幅畫恰好描繪了一條美人魚。法洛爾的“美人魚”很像經典的美人魚形象,有著長長的海綠色的頭髮,一張可愛的臉,裸露的腹部在腰部變成了一條藍/綠的尾巴。然而,這條美人魚的面板是深色的(帶有一點綠色的色調),這意味著它與當地土著居民有相似之處。
在與法洛爾的原畫相伴的註釋中,這位荷蘭藝術家聲稱,他“在安汶的家中,把這個塞勒內人放在一桶水裡活了四天”。法洛爾的兒子從附近的布魯島把它帶給了他,“他在那裡花了兩英制布從黑人手中買下了它”。最後,這隻嗚咽著的動物死於飢餓,“不想吃任何東西,既不想吃魚,也不想吃貝類,也不想吃苔蘚或草”。在美人魚死後,法洛爾“好奇地前後抬起它的鰭,發現它的形狀像個女人”。法洛爾聲稱,該標本隨後被轉交給荷蘭並丟失。這個故事才剛剛開始。
出生於法國、現居阿姆斯特丹的書商路易斯·雷納爾甚至在他的著作《泊松》(1719)中出版了一個版本的法洛爾的《塞倫娜》,在那之前數年,法洛爾的作品就已經廣泛傳播了。然而,由於法洛爾的畫中異常明亮的色彩和奇異的生物,許多人懷疑它們的準確性和真實性。雷納德尤其擔心法洛爾的塞壬的有效性,他驚呼道:“我甚至害怕以美人魚的名義所代表的怪物……需要糾正。
哲學家們在法洛爾的繪畫中發現了希望和厭惡,隨後里納爾在書信中發起了對話。在他1754年版本的《Poissons, ecrevisses et crabes》的序言中,這位荷蘭的動物收藏家和“自然之家”和“自然之家”的負責人沃斯梅爾稱對人魚現實的反對是“軟弱的”,他認為“這個怪物,如果我們必須這樣稱呼它的話(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稱呼它),它比其他任何生物都能更好地避開人類的陷阱(因為它是混血的),因此很少被看到。此外,由於人魚與人類的生物學相似性,沃斯梅爾認為它們“死後比其他魚類更容易腐爛”。儲存的缺乏不僅減少了目擊,也解釋了為什麼陳列櫃裡沒有完整的標本。
此外,由於人魚在生理上與人類相似,沃斯梅爾認為它們“死後比其他魚類的身體更容易腐爛”。儲存的缺乏不僅減少了目擊,也解釋了為什麼陳列櫃裡沒有完整的標本
到了18世紀中期,越來越多的醫生不僅相信人魚的存在,而且開始思考這種生物對理解人類的起源和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正如G.羅賓遜在《自然之美與藝術在世界之旅中展示》(1764)中所指出的,“儘管自然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人魚和美人魚是神話般的動物……就許多作者關於這種生物的真實性的證詞而言,似乎有很多理由相信它們的存在。”四年後,托馬斯·史密斯牧師將羅賓遜的論點寫進了一份更明確的筆記,他斷言,儘管“確實有許多人懷疑人魚和美人魚的存在……然而,似乎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不容置疑。”但問題依然存在:像魯賓遜和史密斯這樣的人只能依靠古老的、經常被嘲笑的目擊事件或脆弱的假設作為他們的“證據”。他們需要科學研究來支援他們的主張,他們做到了。
1759年至1775年間,《紳士雜誌》刊登了兩篇特別重要的文章——每一篇都是透過獨特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魚的。第一件作品發表於1759年12月,與一幅畫有“美人魚”的圖一起。據說曾於1758年在聖日耳曼(巴黎)博覽會上展出。作者指出,這個塞壬是“從生活中汲取的……作者是著名的戈蒂埃先生”。雅克·法比安·戈蒂埃是法國印刷工,也是第戎學院的成員,他在印刷科學題材的精確影象方面的技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把戈蒂埃的名字貼在照片上立即獲得了可信度,即使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形象;但即使沒有戈蒂埃的名字附在它上面,它的印刷物和伴隨的文字也以其現代科學方法而聞名。戈蒂埃顯然與這隻生物有過接觸,發現它“大約有兩英尺長,活的,而且非常活躍,在裝著水的容器裡嬉戲,看起來非常愉快和敏捷。
戈蒂埃因此記錄道:“當它處於靜止狀態時,它的位置總是直立的。”它是一隻雌性,五官醜陋得可怕。”正如附圖中詳細展示的那樣,戈蒂埃發現它的面板“粗糙,耳朵很大,背部和尾部佈滿鱗片”。從照片上看,這不是長期以來讓歐洲各地大教堂增輝的美人魚。它也不符合歷史上許多其他博物學家和發現者的描述。大多數人看到的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女性形體,以飄逸的藍綠色頭髮為特徵,戈蒂埃的美人魚完全禿了,有一雙“非常大”的耳朵和“醜陋得可怕”的面容。戈蒂埃的海妖也比傳統的美人魚小得多,只有60釐米(2英尺)高。更重要的是,戈蒂埃的美人魚反映了18世紀中期研究大自然奇妙方面的方法:這個法國人運用了備受尊敬的科學技術——在這個案例中,他仔細檢查了這個生物的解剖結構,並附上了一幅精確的圖畫(與當時其他有插圖的生物非常相似)——將許多人仍然認為是幻想的東西展示為現實。
學者們利用戈蒂埃的出版物來反思人魚的合法性。1762年6月期《紳士雜誌》的一位匿名撰稿人稱戈蒂埃的形象“似乎無可爭議地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然界確實存在這種怪物”。但這位作者有進一步的證據。1762年4月的《法國美居》報道說,前一年的6月,兩個女孩在法國西南海岸附近的海灘上玩耍,“在一種天然洞穴中發現了一隻人形動物,靠在它的雙手上”。事情發生了一個相當病態的轉折,其中一個女孩用刀捅了這隻怪物,看著它“像人一樣呻吟”。兩個女孩接著砍下了這個可憐的生物的手,“它的手指和指甲已經成形,手指間結了網”,並尋求島上的外科醫生的幫助。醫生看到了這個生物,記錄道:
它和世界上最大的人一樣大…它的面板是白色的,就像一個溺水的人……它有著豐滿的胸脯;一個扁鼻子;一個大嘴巴;下巴上裝飾著一種用貝殼做成的鬍子;全身上下都是一簇簇類似的白色貝殼。它長著一條魚尾巴,尾巴的末端長著一種腳。
這樣的故事——經過一位訓練有素且值得信賴的外科醫生的證實——進一步證實了戈蒂埃的研究。由於18世紀的英國人越來越多,因此存在著人魚,而且人魚與人類驚人地相似,需要進一步研究。
1775年5月,紳士雜誌發表了一篇關於美人魚的報道,1774年8月,“一名商人在群島或愛琴海的斯坦奇奧灣拍下了一條美人魚的照片”。就像戈蒂埃1759年的作品一樣,這個標本被繪製並詳細描述。然而,作者也疏遠了戈蒂埃,指出他的美人魚“與幾年前在聖日耳曼展覽會上展出的美人魚有本質上的不同”。在一個特別有趣的事件轉折中,作者利用兩幅美人魚版畫的對比來推測種族和生物學問題,認為“有理由相信,他們是兩個不同的屬,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類似於非洲黑人,另一個類似於歐洲白人”。戈蒂埃筆下的人魚“在各方面都具有黑人的面容”,而作者發現他筆下的美人魚展現出“歐洲人的容貌和膚色”。它的臉像一個年輕的女性;它的眼睛是美麗的淺藍色;它的鼻子又小又漂亮;它的嘴小;嘴唇薄”。
正如歷史學家珍妮弗·l·摩根所指出的,早期現代英國作家依靠兩種刻板印象來商品化和詆譭非洲女性的身體。首先,他們“按照慣例將黑人女性形象與白人女性形象放在一起——因此很漂亮”。在這裡,這位1775年的作者完全遵循了這一觀點,將戈蒂埃筆下的“黑人”和“醜陋得可怕”的美人魚比作他自己美麗的“歐洲人的容貌和膚色”的美人魚。其次,早期現代歐洲人關注非洲婦女所謂的“性和生殖受約束的野蠻行為”,以最終轉向“黑人婦女作為一種文化劣勢的證據,這種文化劣勢最終被編碼為種族差異”。自然學家不僅利用人魚的科學來獲得對海洋生物的自然秩序的更深的理解,他們還利用他們對這些神秘生物的解釋來反思人類——尤其是白人人類——在不斷變化的種族和生物框架中的地位。
卡爾·林奈和他的學生亞伯拉罕·奧斯特丹使分類和合法性的敘述更加複雜。儘管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749年尋找林奈的美人魚時一無所獲,但林奈和奧特丹在1766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採取了自己的行動。在這篇論文的最初幾頁中,他們詳細列出了一長串歷史上的美人魚目擊事件,接下來他們又講述了無數“神奇的動物和兩棲動物”的例項,它們與傳說中的生物非常相似,因此,分類變得很棘手。最終,他們認為這種美人魚般的生物“值得作為一種動物,應該展示給那些好奇的人,因為它是一種新的形式”。這位“分類之父”顯然發現了自然之謎中“有價值”的一塊,它將人類(即使是遙遠的)與海洋動物聯絡起來。同樣重要的是,塞壬·拉克蒂娜進一步模糊了林奈驕傲地發展起來的分類界限,這表明人類也許可以找到與兩棲動物的某種遠親。
十八世紀哲學家對人魚的研究代表了奇蹟的持久和啟蒙時期理性科學的出現。曾經是神話的核心和科學研究的邊緣,現在美人魚和海神逐漸引起了哲學家們的注意。最初,這樣的研究僅限於報紙文章、旅行者的敘述或傳聞,但到了18世紀下半葉,博物學家開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人魚,極其嚴格地解剖、儲存和描繪這些神秘的生物。到18世紀末,美人魚和海怪成為理解人類海洋起源最有用的一些標本。人魚存在的可能性(或者,對某些人來說,是現實)迫使許多哲學家重新考慮以前的分類方法、種族引數,甚至進化模型。多名歐洲思想家相信——或者至少認為——“這樣的怪物確實存在於自然界”,啟蒙運動的哲學家融合了奇妙和理性來理解自然世界和人類在其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