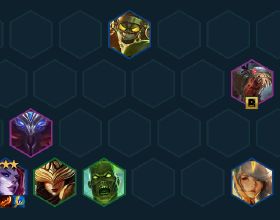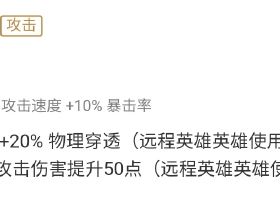●李根萍
熄燈號準時響起,光明山下熱鬧了一天的軍營的夜晚仍如往常,幽暗里長著寧靜,寧靜裡睜著許多雙眼睛。有風從山上急吼吼地下來,挑逗懨懨欲睡的桉樹,撩撥憨厚老實的芒果樹,在炮營八二無後坐力炮連門口的草地上打滾,似乎故意弄出動靜,暗示兵們它來了,它真的來了。原來風兒有時也怕孤獨,總是想方設法顯示存在感。
我們常開玩笑,光明山一年刮兩次風,一次半年。山裡生活久了,要是沒風,似乎總感覺少些什麼。
連隊後面工具棚裡蟲子的呢喃,翻越矮坡,鑽進躺在床上兵們的耳朵裡,卻怎麼也不會住進一個兵的心裡,再吵也沒人會拿蟲子說事。因為每個兵的心事實在太多,裝不下了。
營部那隻黃狗從甘蔗林裡衝出來,一本正經地對著新上崗的哨兵叫,叫過後發現似曾相識,著同樣服裝,背熟悉的槍,便趕忙止住聲,回到營部屋簷下歇息。數只鳥兒在操場邊的樹林裡沉睡,忽然一陣風撞碎它們的夢,撲楞楞從樹枝上跌落下來,在草地上滾了幾下,又跳了幾步,方才從夢裡走出,而後再次飛上那根熟悉的樹枝,那裡臥著一縷柔和的月光,不一會鳥兒又合上眼皮,連同合上了山頂那枚月亮,還有山下整個軍營。
二十多個兵擠在一間排房裡,散發出濃濃的雄性荷爾蒙的味道。風打竹林,蟲吟淺唱,最能撥動兵們內心深處那根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光明山遠離鬧市,閉塞偏僻,交通不便,津貼微薄,被人視為“窮當兵”,許多人情感世界一片空白,久久難以脫單。
班裡比我早一年的福州兵入伍前就談了個物件,正處熱戀期。每週女朋友都會給他寫信。每晚熄燈後,唯有他打著手電在蚊帳裡看情書,兩頁薄薄的信紙,翻過來,翻過去,百讀不厭,讀得心花怒放,讀得如痴如醉,讀得月兒嫉妒,讀得蟲子不想作聲,讀得全排房的人睡不著。睡上鋪的人不停地翻身,床鋪的響動趕跑了窗外夜晚的寧靜。
早上起來,睡眼惺忪,腰帶搭在臂上,在連隊門口桉樹下的小便池方便,一點也無需避諱什麼,因為山裡營區沒有一個異性,全是清一色的男爺們。常有老兵說,這個鳥地方,母豬賽貂蟬,光明山都是公的,山下的蚊子也是公的,每棵桉樹都是公的。起始不太明白其意,漸漸方知,山裡當兵,長年累月難以見到幾個異性,出去一趟也不易,是個實足的“男兒國”。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有了愛情的滋潤,再苦的日子也是甜的。福州兵特意買了把吉他,每天晚點名後,山裡月光如水,他喜愛抱著吉他,帶上馬紮,坐在桉樹下彈唱,多是彈的情歌,為他心上人彈的。記得彈唱最多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營區的兵們聽了他的彈唱,這群單身狗心裡如貓抓似的,說不出啥滋味。
我住光明山,君在大山外。日日思君不見君,唯有山風營區過。兵們正值十八九歲的年齡,軍旅芳華初綻,許多人非常想認識個女朋友,期盼有真摯戀情慰藉單調枯燥的歲月。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天天窩在這大山裡,哪有機會呢?
班裡江西籍副班長服役第五年,年底有機會轉志願兵,本來想轉了後再回去相物件,山裡實在難熬,家中也一再來催,他提前請假回家了。十天後,副班長還真帶女朋友進山了。江西妹子,高挑清秀,落落大方,當我們叫她嫂子時,她臉上立馬泛起一朵朵紅雲,煞是好看,宛如年畫裡的明星。
晚上熄燈後,教導員來查鋪,發現副班長還沒回來睡覺,便命令班長去叫。班長猶豫再三,便差我去。此事顯然都不想去,可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不去就沒個鳥數,我只得受領。連隊的家屬房立在連隊後面的菜地旁,木棉樹下第一間平房裡正亮著燈,這是我幫副班長早早整理好的房子。想著副班長好不容易脫單找到物件,女朋友第一次來隊,肯定有談不完的話,訴不完的情,此際去敲門,肯定掃興,弄不好還會挨他批。走到半路,我還是折回了。
我回到排房躺下不久,副班長陰著臉回來了。班長看了我一眼,我沒吱聲,或許他想著是我辦的“好事”,我當然不會說實話。不過那天晚上,副班長翻了好久才睡著。
第二天早上跑步回來,我和班長迎面碰見教導員,他當場批了班長,我知道你們不會去叫副班長,要是出了事,看我不收拾你。幸好我親自去一趟……班長回頭看我一眼,但什麼也沒說。
那個年代,老兵將物件帶到部隊,如果在一起過夜了,後來要是反悔,女方就會來部隊告狀,尤其是轉了志願兵或考上軍校的,部隊一般會讓其選擇,要女朋友還是要軍官或志願兵,最後都只得妥協。教導員有經驗,怕老兵惹事,沒有領證,總是當惡人,到點就板著臉趕人。
連長比副班長年齡還大,也是一條光棍,天天和我們泡在一起,如果誰嘆息沒女朋友,他就會笑我們沒出息。教導員一直關心連長的婚事,後來竟然下令將他趕了回去。連長回到老家半個多月後拍回電報,讓我開車去駐地旁的盤陀嶺下接他。
盤陀嶺有條國道直通連長的老家廣東。果然在約定的時間,連長從大巴車上下來,後面跟著一個姑娘,不用猜就是連長的女朋友,小巧玲瓏,五官端正,白白淨淨,與面板黝黑的連長反差實在太大。我開心地笑著迎上去,接過女子手上的包,親切地叫了一聲嫂子,女子害羞地低下了頭,不好意思看我。
車還未進營裡,教導員得知後,早早就在連隊門口等候,連隊的兵們圍上來,像是迎接上級重要的客人。那個年代,軍人不易,找到物件更不易,值得可喜可賀。
連長女朋友來隊,也住在家屬房。連隊的兵們種菜或訓練之餘,有事沒事會去看看嫂子。嫂子帶來許多糖,來人就抓一把。當時連隊要是找不到人,老兵們就會調侃,肯定又是去看嫂子吃糖去了。大家聽後哈哈大笑。要是給連長聽到,會隨口罵我們,這些小子,就這點出息。
一個週日,沒有任何徵兆,班裡的福州兵收到女朋友的信後,當場失控,哭了,衝出排房,在桉樹下傷心徘徊。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原來他失戀了,女朋友讓他回去陪陪她,福州兵無法請到假,儘管一再想挽回,但女方心意已決,鐵定分了手,連過去的信物都全部退回了。那時兵們失戀,乃家常便飯。
自那天起,福州兵再也沒在桉樹下彈《月亮代表我的心》,因為“月亮”不屬於他了,情已斷,愛已盡,真已假。他的吉他扔進了連隊倉庫,任灰塵覆蓋,任蟲子滾爬。
光明山下的情事,三二句寫不完。不過我還是喜歡詩人郭小川的詩:軍人自有軍人的愛情,忠貞不渝,新美如畫。
光明山,光明山,進山一片光明,出山光明一片。
3年後,我奉命出山,北上學習。連長已和女朋友成婚,嫂子在老家工作;副班長年底 轉了志願兵,和江西女子生了個胖小子,虎頭虎腦,可愛極了;福州兵第二年退伍了,從此失去聯絡,不知他過得好不好。那時沒有網路,沒有微信,每次出差福州,想找他都未成,不過我真誠為他祝福,為光明山下的每個戰友送上祝福。
山裡奉獻的歲月或短或長,是一生之自豪,因為歲月靜好,需要有人默默地付出。請記住光明山裡的一切,記住一團有情有義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