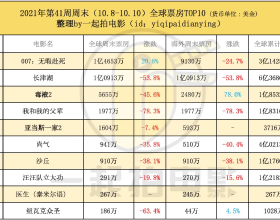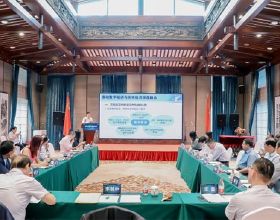1980年,距離新中國成立已然過去了差不多30多年的時間了,對於大多數的共和國將領大多都步入了花甲之年,祖國富強、兒孫滿堂、共享天倫之樂已經成了他們現如今最好的期望。
而在這一年的一天,兩位家鄉紅安的政府工作人員在將軍樓聯袂拜訪了已經63歲的開國少將肖永銀,在一番寒暄後,工作人員從公文包裡拿出了一份紅標頭檔案,說道:
“將軍,我們來談談你父親的問題吧!
言罷把檔案輕輕地攤在了面前的茶几上,此時的將軍戴上了老花鏡,掃了一下面前的檔案,這時身經百戰,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將軍身子明顯的微微顫抖了起來,將軍拿起檔案再次確認了一下內容:
“肖永銀之父肖治學於1930年在大別山肅反中不幸遇難,先予以平反......。”
當老將軍看完,抬起頭時,政府工作人員發現將軍的眼眶似乎有東西在逐漸醞釀、滾動。
父親啊父親,是既陌生又熟悉。一想起父親,老將軍心裡就一陣翻滾,心情是一陣煩躁,想當年父親蒙難之時,他只有區區的13歲,母親早亡,父親又遭此劫難,一個孤兒在吃不飽穿不暖能活下來已經是個奇蹟了,由於年代久遠父親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
就在將軍雲遊天際之時,工作人員又從公文包裡取出了200元,並適時地打斷了將軍的思緒:
“將軍,這是縣政府給您父親的安葬費。”
首長,你還有其他的要求嗎?可以提。這是一句結尾的例行問話,一般處理冤假錯案,家屬一般都會要求經濟的補償或者一些附加條件,只要條件不過分,一般都會滿足家屬所提出的要求。
老將軍沉默著,最後低沉地說了一句話:“我是講政治的,不是講鈔票的。”
此時的將軍心裡一陣複雜,畢竟人死燈滅且屍骨無存,就算有再多的金錢又有何用,現在最重要的沉冤已經昭雪,名譽已經恢復,這就已經夠了。
冤情已經平反,父親在天之靈也應該可以瞑目了。那麼當年將軍父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13歲就成了孤兒的肖永銀又該何去何從。
赤色的土地,將軍的搖籃
將軍和將軍父親降生於一塊共和國的“福地”。
在這塊赤色的福地裡一共誕生了幾百位共和國的高階優秀將領。其中董必武、李先念等為文,許世友、秦基偉等為武,真正做到了集天地之靈氣,孕育亂世之英才。
特別是918事變後,祖國山河崩碎,短短時間內大半國土盡喪敵手。就在此時,一支影響後世千秋萬代的紅色部隊應運而生,它就是紅四方面軍。
紅四方面軍在日寇的炮火中呱呱墜地,從此踏上了一往無前的步伐,當地的青壯年數以萬計地加入到這支紅色部隊中來,組成了其鋼的骨骼,在締造共和國一系列光輝的戰役中,他們的忠骨遍佈於長征途中的雪山草地,敗走麥城的東征河西走廊,散落於巍巍太行,埋葬於莽莽中原。
而這個地方就是以前的黃安現在的紅安。而之後的人口普查更是彰顯了黃安為新中國勝利所做出的巨大犧牲:
“據當時的人口普查記載,當時黃安一共繁衍生息48萬餘人,經過一系列戰役後直至新中國成立,黃安所剩下的人口數已經不到區區的10萬餘人。”
而時至今日,現在的紅安還流傳著一首膾炙人口的民謠:
“黃安小縣,銅鑼一響,四十八萬,男人打仗,女人送飯。”
不難想象當時的黃安民眾驅除韃虜,全民皆兵的盛況,而後來國民黨在黃安縣的黨部還發過佈告,其中寫道:“十歲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無長上。黃安素為禮儀之鄉,現為禽獸之所。”
可見當時的國民黨對黃安已經失去把控,黃安已然成為了紅色地區,且已經深入人心,而肖永銀和父親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地區。
父子陰陽相隔
綿綿數百里的大別山脈南邊有一處地方叫黃安縣肖家灣,而1917年6月某一天的寅時,下著雨,一處農家小院卻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情緒,但隨著響亮的幾聲哭喊,一切都煙消雲散,因為男童降生了。
男童的父親名叫肖治學,略通筆墨。他看著此時窗外正下著雨,所以給孩子取了乳名叫雨生,又因為生在寅時所以取名肖永寅,這是當時當地通常的取名手法。
而在我國夜與日的接替3時到5時統稱叫寅時,這時候天色微醺,天色似明未明,是黑暗迎接光明的時刻。而父親肖治學給他取名肖永寅也飽含了對其的殷切期望,希望他永遠嚮往光明,驅除黑暗。
雨生的出生給這一家增添了許多的歡聲笑語,雖然那時候生活清貧,但是一家人是苦中作樂,倒也是其樂融融。
然而命運最是喜歡跟人開玩笑。這份難得的幸福快樂在雨生5歲的時候,因為母親的病逝而戛然而止,小雨生只有跟父親和大自己7歲的長兄相依為命了。
母親的驟然離世,讓一家的重擔全部壓在了父親一個人身上,夏種稻子冬種麥,父親極力地呵護著幾畝微薄祖田,就算這樣一家人也只能勉強裹腹而已。
雖然平時照顧兄弟倆,耕種已經是非常辛苦,但是父親依舊加入了村委員會(紅色政權組織),在開會期間擔任會議記錄。當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父親都是秘密進行著活動,畢竟當時的黃安雖然是紅色覆蓋區,但依然有反動派在進行活動。
父親有著自己的秘密,而逐漸長大的雨生也跟父親一樣也有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加入了童子團並擔任了隊長一職,就這樣父子之間有利彼此的秘密,但又各自守護著秘密,互不干涉。
原以為這一切都會有條不紊地繼續下去的時候,1930年春一個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一天,把一切的平靜都給打破了。
已經13歲的雨生已經可以幫著父親一起在水田裡插秧了,周圍也都是鄉親們忙碌的身影,而就在這時水田邊來了兩個人在田埂旁就是一陣大喊:“肖治學,肖治學。”
聞訊的父親連忙把手裡的秧苗塞到了雨生的手裡,一腳深一腳淺的朝岸邊走去,甚至連鞋子都沒穿就跟著二人經消失在附近的山間小道里了。
看著水田裡父親留下的腳印,雨生也沒有多想,以前也試過幾次父親急匆匆地趕去開會,但是不管多晚,父親都會趕回來,雨生以為這次也不會例外。
所以,雨生並沒有好好的跟父親道別,甚至沒有說上一句話,只是在父親閃進山道之時急匆匆的撇了一眼,就重新彎下腰把父親未插完的秧苗直至全部插完。
而當晚父親徹夜未歸,沒想到父子二人水田一別,竟然陰陽兩隔。而父親臨別時,父子二人沒有隻言片語的交流也成了雨生心裡永遠的痛。
後來村子裡又相繼“失蹤”了幾個人,而這也讓村民們更加議論紛紛,而最為痛苦的就是像雨生這樣的失蹤者家屬了,沒有道別,沒有遺言,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連遭打擊,驚魂一夜
13歲本該是天真爛漫的年紀,但雨生卻不得不接受成為了孤兒的現實。哥哥年長7歲現在已經20歲了,由於雙耳染疾有著嚴重失聰,好不容易娶了媳婦,所以父親把家裡唯一的一間屋子給了哥嫂住,而雨生和父親就只能住在四處漏風的牛棚裡。
現如今父親失蹤已成現實,牛棚也徹底沒有了父親的身影,雨生只能獨自承擔。為了早日擺脫喪父的陰影,這一天雨生揹著書包前往學堂上學,但這一路昔日的玩伴不是以異樣的眼光看著他,就是像躲瘟疫一樣躲著他。
快到學堂門口時,昔日童子團的團長攔住了他,用稚嫩的口氣對他做了通牒:
“肖永寅,你被開除了。”
此時的雨生只能緊握著拳頭,強忍著不流下眼淚跑回了家裡。此後的日子,學也上不了,童子團也沒有了一席之地,雨生終日只能跟牛作伴了。
如果只有孤寂和悲慘作伴,那麼雨生的這一生註定是平凡的,但是年幼喪母,近期又遭遇父難,這讓他那孤寂的心房多了一絲警覺,這足以改變他的一生。
而這一天,勞作了一天的雨生傍晚趕著牛回到了牛棚,這時候哥嫂走了過來跟他說:“雨生,有人找你。”
自從父親出事之後,大家對他是避之不及,而現在嫂子卻說有人找,這不禁嚇得雨生面如土色,而這也不禁讓他想起了父親在水田被人叫走的情景。
哥哥看到雨生嚇成了這樣,不禁搖了搖頭,對雨生說道:“放心,不是來抓你的。”哥哥不說還好,一聽到哥哥這句話,雨生趕緊嚇得撒腿就跑,現在他心裡就認定了一個理,哥哥是殘疾人,嫂子是女人,不可能抓他們,那麼肯定是來抓自己的。
雨生沿著村道,一路跑一路隱蔽,東躲躲西藏藏,最後都覺得不安全,最後決定冒險回到了家裡,趁著哥嫂不注意跳下了自家的糞坑裡,讓惡臭把自己隱藏起來。
就這樣,雨生一直躲到了下半夜。起初,在院子外面還不停地有腳步聲和狗吠聲傳來,後來就再也聽不到什麼聲音了,此時的雨生餓得前胸貼後背,他踉踉蹌蹌的爬出糞坑,再次凝視了生活了13年的家,他覺得時候離開了。
月光的餘暉灑在清冷的村道上,就算雨生一路小跑也覺得甚是清冷。這時候他緊貼在一間茅草屋聽了一會,然後迅速的繞到了門前並輕聲的叫喚了起來:“奶奶,奶奶,我是雨生。”
不一會兒,屋內的煤油燈就亮了起來,奶奶趕緊讓雨生放了進來,此時的雨生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還散發著一陣惡臭,看著孫子一副驚魂未定的模樣,奶奶流下了兩行濁淚。
“奶奶,有人要抓我。”無助的雨生緊緊地抓住了奶奶的手。奶奶嘆了口氣說道:“人家抓你這個小娃娃作甚。”
“真的,哥哥是殘疾的,嫂子是女的,肯定是來抓我的。”看著雨生說得一板一眼,奶奶心底不由一陣抽搐,不由抱著雨生哭了起來。
待雨生的情緒有所穩定,奶奶趕緊端來水、衣服、食物,解決了雨生的溫飽問題。“奶奶,我要離開村子了。”雨生說完拿起屋內的舊草帽就要出門,奶奶趕緊攔住:“你那麼小,能去哪。”
“我告訴您,您不要告訴別人。”雨生踮起腳尖在奶奶耳邊一陣耳語,言罷,拿起草帽往頭上一扣,就轉身離開了。
毅然從軍,書寫傳奇
離開肖家灣的雨生,走了4里路,來到了小集鎮。這裡是紅一軍也就是後來的紅四方面軍的募兵處,雨生早有耳聞。
“你叫什麼名字?”“肖永寅”
此時的紅軍募兵處的戰士卻筆誤地把寅寫成了銀,而這也重新書寫了人生新篇章,從此少了一位肖永寅卻多了一位肖永銀,那一年是1930年,那一年他13歲。
而回過頭看看造成這次轉折的抓人行動,一切都是虛驚一場。就算當時情況再怎麼複雜,也斷然不會牽扯到一個13歲的孩子身上,但這次所造成的結果確是始料未及的。
肖永銀從軍很快就嶄露頭角,歷經幾次反圍剿,爬雪山過草地,幾經生死、屢遭磨難,最後作為軍長揚威朝鮮,成為共和國最為優秀的將領之一。
1955年肖永銀被授予開國少將,被寫進了歷史。但滾滾紅塵泯滅的生靈又有何其多,而他的父親只是其中的一個,一個基層的共產黨員,一個被歷史塵封的人,烈士檔案查無此人,甚至連犧牲在何地都無從查證。
無墳、無屍、無碑,這也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遺憾,但現在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最為主要的是名譽已經恢復。
人有枉死,但歷史終有公正。這是年輕政黨必須所經歷的過程,摸著石頭過河,哪個早期的共產黨人不是幾經生死考驗,甚至殺身成仁的都不在少數,而像軍父親只是千萬人當中的一個,此時此刻被收進共和國的烈士名錄或許是對其最好的告慰了吧!
謹以此文獻給為了新中國而犧牲的無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