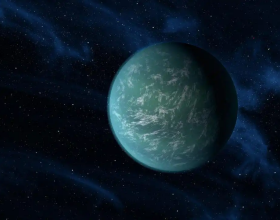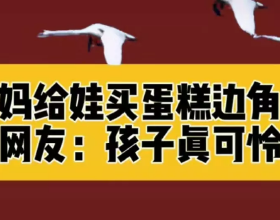吃貨們的十一假期,卻是嘴巴的加班周。朋友宴席上的佳餚、鄙陋小巷的小吃、自己做的拿手菜……這個假期,最讓你忘不了的美食記憶是什麼呢?
我們喜愛美食,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食物與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有某種特殊的關聯——它可以提供特殊的記憶、生活中的慰藉和掌控感,乃至個人的文化認同……換句話說,食物彷彿一枚特別的“碎片”,從中可以湧現出一個人的全部的“生活世界”。
然而,今天的食物與生活世界的聯絡正在被打破。“現在很多食物缺少陽光和鄉愁的味道”,我們常常聽到類似的感慨。與這種危機相伴而行的是,食物的呈現方式也逐漸趨向“奇觀化”:一方面,社交媒體上充斥著”網紅餐廳”的盛景影象,縱然它們往往不能提供優質的飲食體驗,卻也總有人願意為之買單;另一方面,那些曾默默無聞,作為計劃經濟孑遺和公有制象徵的食堂也在近期頻繁作為奇觀出現:醫院、機關單位的食堂製作的月餅在今年中秋節期間受到追捧,甚至被哄搶抬價和仿冒……
本期讀刊,我們和大家聊聊食物在味覺享受之外的獨特意義。在下文中,作者藉助德國哲學家本雅明的“靈韻”思想,分析食物如何在前現代社會建立起人與生活世界的聯絡;為什麼這種聯絡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淡薄;而食物呈現上愈演愈烈的“奇觀化”現象又是如何產生的?
聯結世界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總能在食物中找到慰藉?
“食物是很安全的享受,人們可以毫無恐懼地在其中放鬆自己,在其中找到自由與慰藉。”《魚翅與花椒》的作者扶霞·鄧洛普曾這樣說。
在筆者看來,食物與生活世界的關聯主要有兩種體現方式。第一種方式如鄧洛普所說,食物部分充當了作為整體的生活世界的維繫者——讓人們意識到,生活世界是安寧的,可掌控的。

《魚翅與花椒》,[英] 扶霞·鄧洛普著,何雨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版。
如果說在第一種情況下,食物支撐起的是作為整體的生活世界,那麼在第二種情況下,食物可以與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如特定的時空地域、記憶片段,乃至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發生關聯。例如,《晉書·張翰傳》便提到“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正因為鱸魚和“秋風”“吳中”之間的關聯,才有了“蓴鱸之思”的典故。而魯迅的文章《社戲》則將食物與童年往事,幼時玩伴聯絡在了一起。
無論是哪一種方式,食物常常能與我們與世界之間建立起特殊的關聯,可能是一段兒時的故鄉回憶,或是建立一種文化認同,帶來心靈的慰藉。食物的這種特殊性,用本雅明的話來說,可以稱之為食物的“靈韻”。
“靈韻”是本雅明用來談論藝術品的概念。 在本雅明眼中,靈韻關涉到作品的“語境”,意味著作品的獨一無二和不可複製。藝術品的誕生、存續和展示都離不開獨特的語境,而靈韻正是被這種語境所造就。例如,某一大師的畫作獨一無二,任何複製品都無法取代本尊;這是因為大師只對原作傾注了他的創造力,也只有原作,才在其誕生、存續和展示的過程中經歷了獨特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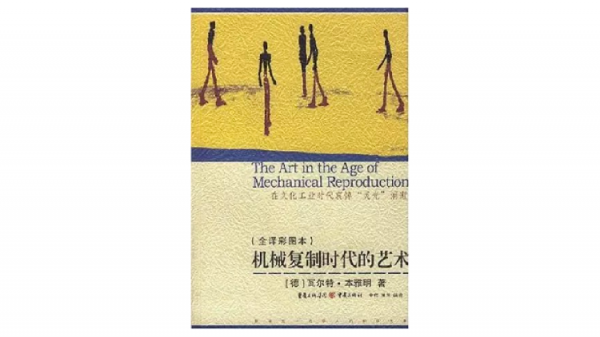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瓦爾特·本雅明著,李偉譯,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
在這種意義上,本雅明用以形容藝術的“靈韻”同樣適合於食物。幾乎在所有人眼中,總有一些食物承載了特殊的意義,而這種意義來自於它們與人們生活世界之間的具體關聯。由此,這些食物具有了獨特的、區別於其他食物的靈韻。
並非所有的食物都同等地具有“靈韻”,具備“靈韻”的食物往往也具有特殊性。例如,筆者的祖母喜歡在西紅柿雞蛋湯中加入裹著蛋清的肉餅,而這樣的做法並不常見。正因如此,筆者只有從這樣的西紅柿蛋湯中才能感受到“靈韻”,而餐館中其他做法的蛋湯都僅僅是西紅柿蛋湯而已。
如果說靈韻以特殊的食物為載體,並具有多樣的體現形式,那麼,又是什麼賦予食物以“靈韻”呢?這關係到傳統社會的食物生產方式。
首先,在傳統的食物生產模式中,人參與了食物生產的大部分流程——從食物的採購,到原材料的製備,再到成品的製成。某些時候人們甚至會參與食物的種植和養殖。正因參與了食物生產的全過程,人們才可能從中找到對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實現的滿足感。相比之下,當下生活中的許多工作已然在分工體系下被拆解得七零八落。正如盧卡奇所說,在高度分工的情況下,人們失去了對工作全流程的“掌控”。同時,從事簡單重複的機械運動,也難以令人們獲得自我實現的滿足感。正因如此,食物維繫了一種難得的“整體”感,部分地使人免於意義的缺失和經驗的支離破碎,“貼上”起了作為整體的生活世界。
其次,傳統的食品生產大都是在自然的共同體——家庭和傳統社群中進行的。黑格爾認為它們“自然的倫理實體”——用簡單的語言來說,家庭成員以及社群成員之間都有一種天然的親密關係。正因如此,自然共同體的成員們會在製作、享受食品的過程中不分彼此,親密合作,共同分享。如果說當下的生產分工,如盧卡奇所指出的,會帶來一種“靜觀”和“孤獨”的態度:每個人僅僅完成自己的部分,對他人的活動漠不關心——那麼在自然共同體中,情況恰恰相反,人們集體參與食物的製作,分享最終的成果。即便有一些成員不直接以勞動的方式參與,他們的態度也絕非“靜觀”。因此,食物與特定的人物、記憶發生了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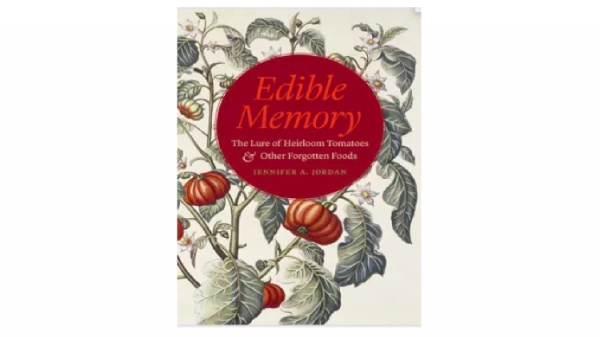
Jennifer A. Jordan, Edible Memory: The Lure of Heirloom Tomatoes and Other Forgotten Foods, 201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另外,自然共同體的“特殊性”也在食物中得到了體現。一方面,由於置身特定的環境,自然共同體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色。正因如此,食物會帶有“鄉愁”的味道。此外,自然共同體沒有采用大規模、機械化的生產方式,它們的食品生產也非是為了滿足普遍化的商業需求,而是為了滿足具體成員的各不相同的“口味”。因此,自然共同體製作的食品,從製作方法到口味,都是特殊的,每一餐都是“獨一無二”的。
由此,在傳統的食品生產方式中,食物之“靈韻”的各種特點都能得到解釋:生產方式的整體性帶來了掌控感;生產方式的自然共同體屬性則揭示了食物與生活世界何以發生聯絡。然而,恰恰在當下,隨著食品生產方式的調整,食物的“靈韻”也處在危險之中。
當食物與生活世界脫節:
標準化生產、景觀化外形、人造“靈韻”運動
正如人們所感受到的,食物的“靈韻”處在危險之中,而“靈韻”的消逝又首先來自於傳統食物生產方式的消逝。
在當下,食物的生產幾乎也進入了“機械複製時代”(本雅明語),大多數餐廳都採用了標準化的食物配比和調味方式,甚至直接以料理包,或中央廚房提供餐食。這些做法旨在以標準化,大規模的生產來儘可能適應標準化,普遍化的“口味”,進而塑造標準化、普遍化的“口味”。
由此,人們一方面不再參與食品生產與製作的流程。不僅消費者變成了單純的“食客”,就連生產者也未必參與了食物產生的全部流程,而是僅負責其中的某一步驟。因此,這樣的製作流程不再為人們的自我實現和掌控感留下空間。相反,人們對食物的態度變成了單純的“靜觀”和“吞嚥”,更因為與生產流程的分離,人們對於經過重重不透明流程,最終到達自己手中的食物反而多了一份“猜忌”和“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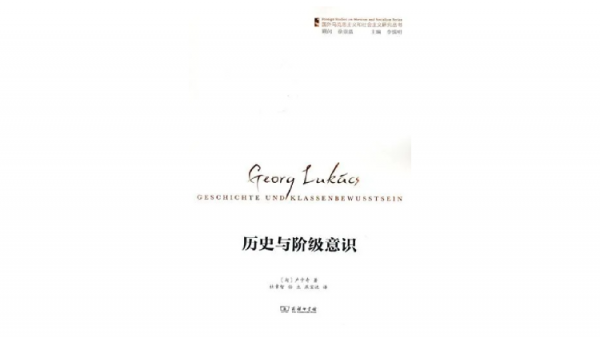
《歷史與階級意識》,(匈)盧卡奇著, 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其次,以如此方式生產的食物也不再針對具體的人和他的“口味”。相反,這樣批次化製作的菜品旨在滿足更加普遍化,標準化的味蕾。如果說食品的靈韻本身也需要影片的獨特性來承擔,那麼在機械複製的時代,這樣的“靈韻”也隨之消失。
正如藝術的機械複製時代消解了藝術品的“靈韻”,食物“機械複製時代“的到來也令“靈韻”處在危險之中,令食物與生活世界之間的關係不復存在。在當下,當食物向人們呈現自身時,它們不再是一枚濃縮了生活世界的碎片,而是一幅充滿誘惑的“景觀”。在這樣的“景觀”中,“靈韻”本身也常常被挪用為一種賣點和噱頭,被收編為消費主義的符號。
對於食物的“景觀化”,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感到陌生。“景觀化”將人們的注意力從食物本身轉移到符號意義和“表徵形式”上。例如,奶茶店僱人排隊,打造“門庭若市”的假象在業內已然是“標準動作”;而一些“網紅日料”更是營造視覺盛景的好手:將切片的牛肉堆成紅白相間的小山(雖然肉片之下小山主體部分是冰塊);選單上滿滿鋪排著高畫質、高飽和的美食特寫;另一些網紅餐廳更是將“乘船用餐”“漢服拍照”作為賣點……而在種種景觀中,製造“靈韻”往往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
一個例子是,不少糕點店鋪都青睞“手作”的賣點。彷彿在“手作”的標籤之下,每一份商品都具有了獨一無二的屬性,承載著獨特的匠心和文化內涵。此外,帶有靈韻的食物往往承載地方性文化,而這些地域文化的符號也被廣泛挪用:湘菜館子裡必定裝點著成串的紅辣椒,港式茶餐廳裡也少不了寫著繁體字樣的招牌……彷彿透過符號的堆砌,它們所售賣的菜品也重新獲得了靈韻,恢復了與生活世界的關聯。
然而,恰恰在這種製造“靈韻”的運動之下,掩藏著一種自我顛覆的邏輯。無論如何堆砌符號,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由於生產方式的變化,這些餐廳註定無法留住真正意義上的“靈韻”。因此,越是吸引那些為追尋“靈韻”而來的食客,這些食客也就越容易在這些符號的“提醒”下意識到靈韻的喪失。由此,食客並沒有真正被“偽造”的“靈韻”“遮蔽”,而僅僅是出於無奈:身在異鄉的他們或許依然會前往這些餐廳,在各色符號中享受一場置身生活世界的夢境,但對於“靈韻”的喪失,他們也同樣心知肚明。
搖擺在消費主義與生活世界之間:
食堂月餅為什麼受歡迎?
被“製造”的“靈韻”之所以被人接受,一方面是由於“景觀”確實俘獲了人們的眼球,甚或是部分地塑造了人們看待食物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許多人接受被製造的靈韻也是無奈之舉。正因無奈,他們試圖以某種方式挽留真正的靈韻。在這種姿態的驅使下,一種新的消費趨勢開始出現:近段時間,單位食堂開始廣受追捧:例如在中秋之際,人們驚訝地發現,相較於被刻意打造成景觀的網紅月餅,這些單位食堂製作的、帶有計劃經濟孑遺和公有制痕跡的月餅用料紮實,價格實惠。因此頗受歡迎。
的確,作為公有制的孑遺,食堂並不需要像一般餐廳那樣,在成本-營收的問題上秉持著嚴格的理性計算精神斤斤計較,甚至犧牲食品安全來實現成本管控;更無需將自身“景觀化”,進而虛增自身用於營銷宣傳的資源。正因如此,食堂可以做到“安全放心”,也可以做到“價廉物美”。
但更有趣的是,除卻價廉物美,食堂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靈韻“的守護者,部分地恢復人與生活世界的聯絡。以校園食堂為例,在高校食堂中,食堂師傅屬於“職工”的序列,他們與學生的交往遠比單純的商品提供者與消費者更加密切:很多時候,學校會創造機會,讓師傅和學生一起參加晨跑、讀書等活動,一些地域性學生協會也會與當地籍貫的食堂師傅有所聯絡,即便是在打飯購餐的過程中,一些比較外向的師傅也會樂意與同學們攀談。而更加頻繁,日常化的交流使得學生的個性化口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例如,很多同學都會回憶,一些常去的視窗的師傅會認識自己,甚至記得自己的飲食偏好。同時,學生自己也可以在特定的時機參與到食物的製備過程中,不少高校都有後廚參觀、廚藝比賽等活動。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食堂所在的校園或單位本身便構成了一個具有整體性的生活世界,而食堂作為這一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所生產的食物也自然而然地與之發生了關聯。在這些食物中,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充實,而沒有被抽象為普遍的、標準化的商品交換關係。
這樣的食堂模式如今已不那麼常見。但毫無疑問,在許多年前,這樣的就餐模式是大多數人的“日常”。因此,“食堂”的名號在今天仍然能喚起人們的回憶,乃至一種“歸鄉感”——食堂製作的食物足夠可靠,甚至可以從中構築出人和生活世界的整體性關聯。因此,對於有過食堂回憶的人而言,食堂在今天依然帶有“靈韻”;而即便對於沒有這類回憶的人來說,食堂的價廉物美也足以成為一種吸引力。
然而,這樣的文化符號在今天也處在“爭奪”的焦點之中,在很多時候同樣會遭到“收編”。例如,許多餐廳熱衷於將自己命名為“XX公社”。它們用上世紀風格的搪瓷杯,領袖畫像,宣傳畫,乃至頗具時代感的服務員著裝來裝點自己,嘗試營造某種“公社感”。同時,單位食堂製作的月餅也會在持續的營銷曝光下成為新的景觀,並被哄抬出遠超所值的高價。正如今年中秋節火爆的“精神餅”,這款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醫院食堂推出的月餅,反而因為它與“精神衛生”之間的聯絡成為了狂歡的焦點,甚至被冠以“精神餅”之名,遭到炒作哄搶。因此,在追捧食堂之時,人們依然搖擺在“靈韻”與消費主義構築的景觀之間。
阿格妮絲·赫勒曾提及現代性之下“故鄉”的消逝,而食物之“靈韻”的命運也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這一過程的註腳。如果說古人還可以在“蓴鱸之思”中借食物的靈韻找到自己與故鄉的聯絡,那麼在當下,靈韻的消逝不免令人發出更深層的,“何以為家”的嘆息。
作者 | 謝廷玉
編輯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