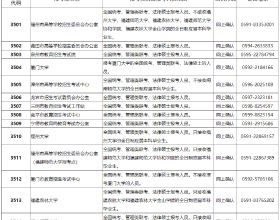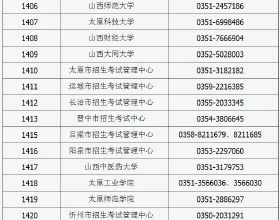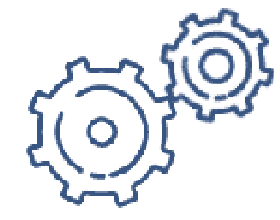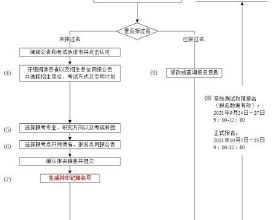審視湯淺政明的作品與《普羅米亞》的區別,兩者有什麼不同之處?
一直以來,湯淺政明的作品令我感動的是電影和動畫「和而不同」的地方。
動畫的線條運動取代排程和攝像機運動,也可以說,影象的單位必須再重新定位,回到變形這樣原始或原型的基質。線條是區分內在/外在的界線,在變動中因其韌性與脆弱而有無限的可能,以線條為單位,湯淺政明進而處理他反覆的命題:
主人公彷彿歷經一場奇幻的辯證行為治療之旅,加害與被害、傷害與愛、生與死⋯⋯之二元如何被勾勒又消解,又如何暈染出新的交集,令什麼新的方向與界限顯明?也可以說帶有道家的、系統論的色彩,一種湯淺式的「萬物消長與關係之圓」。
後來,他較「商業」的作品,比如改編森見登美彥小說的《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追尋未知與新鮮的少女與追尋少女的學長,看似輕盈把控誤會與錯差的戀愛喜劇,卻也延續了《心靈遊戲》(甚至短片《貓湯》)的生長與殺伐一體,《毒湯》中的靜謐與溫暖。
而乍看較為孩童向的《宣告黎明的露之歌》則是全新的《獸爪》,繼續相信擁有與非人對話和相愛的能力。而我特別喜歡《宣告黎明的露之歌》,迴避了後者中二的世界觀,更有孩子般的灑脫與坦率,人與非人既定的差異也因而扭轉:人魚比人類「更人類」(但不是在「高貴的野蠻人」基礎上)。
能更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身體先行」:人魚露的歌聲先讓人類不由自主地動起來,而後才令他們感到快樂。先身體力行「扮演」,才從心(重新)發覺快樂。湯淺擅長的變形與流動的線條,正是可以讓心與物之間的介面遊移不定,達到兩者新的交集和融合。
此外,他特有的生態觀,也讓差異的個體進入一個更大的同一迴圈之中——海上消失的人變成人魚,被丟棄的流浪狗復活成狗魚,在生締/活締法切下魚骨頭可能會存活下來⋯⋯隨時在流動的食物鏈迴圈,比老布勒哲爾之類的怪誕畫,更生機勃勃。漾動的是澎湃的笑與淚,先於沈思。原本自然界殘酷的「進食/被食」位階,有著快樂與尊重。
進一步來說,甚至像閱聽者和創作者,去消費和消化已成為過往的、精神存在於物質遺蹟的種種。我們更多時候,忘記了所經歷的人與事與故事,但只要被我好好地吃下去,變成我的一部分,或改變了我,無論消化徹底不徹底,它在我體內啟動所牽涉多廣、多久遠,都可能在因循又新的迴圈,自他們傳遞向我,再傳向更多的彼與此。
但反面來看,「人魚驅動人跳舞」,是如此加諸於人的異權,不自由的詛咒/祝福,卻讓人產生享受自由的幻覺。
電影里人們不受束縛的舞蹈,影象的爛漫作畫,觀眾感受到的是一種絕非脫框而出,而是在景框深處那個無比自在的世界,遠在我們屏幕後面有更廣闊的空間,但又絕不屬於我們的自在——以人工的珠貝折映海洋之幽美,動畫無中生有的世界,在那裡的「真實」是一種不可知論的魅力吧。
更近期的《乘浪之約》,延續了《宣告黎明的露之歌》的「水底情深」,上映在東京奧運前、京都動畫公司火災後,有另一種感時之情。湯淺繼續利用著「水,液體,相位變化」來描摹人鬼之戀。
過去漫綿的甜膩溫柔,現時凝滯的悲傷,如水隨形,且隨行而變。
這些變化,在磨咖啡豆精心氣泡之中,在劃開蛋包金黃色暖洋洋蛋液之中,在雪夜時而聚合或時而直落的晶體,在與你初見的水底。事物、生命與關係,是這樣碰撞、生滅:消防隊的長管如扭動的水蛇,對上火舌。要怎麼讓逝去的你與關係現形?電影硬是賦予水形狀,用聲音召喚作為魔法,強行固著了你。這如何持久?有什麼能夠持久的?直到我們真的能乘上下一波浪頭,回到那個更廣闊的地方,是水、是生命的歸處也是去處。
若說湯淺政明的作品是自由的,柔韌變形可滲透的線條,以及線條構成的消長迴圈之圓;《普羅米亞》則是幾何色塊的堅實,卻仍帶有一種爽快地推翻——月滿則虧,盛極必衰,是一種否極泰來的樂觀。
《普羅米亞》的線條並非是獨立存在的單位,重點也不是線上條構成邊界的兩側互相漫延,《普羅米亞》的線條是為事物和概念已經十分僵固的狀態而存在的。這個世界是由分明的幾何構形所構成的——連濛濛光暈灑落都是三角形或方形的——一切規則定義已述明而不可更動的世界裡,人們的作為還有什麼潛能可改變世界、動搖彼此呢?
電影創造了的電車難題,跟它的幾何世界一樣分明。乍看數字構成了人類,如線條為著形狀服務,但當你不斷放大里頭事物到極致,每個微小單位卻是相似的。所謂難題,其實早有了答案,指向那個一致。
先是犧牲少部分的異能者,來換取全人類的福祉,你同不同意?再是,犧牲少部分的異能者,拯救地球上少部分的人,你同不同意?最後這虛偽的難題來到最簡化的版本——犧牲少部分異能者,同時導致所有人的覆滅——你根本不用同意。(這個惡意的起點不過是一種自我厭惡,一種自毀卻擴及他人的自私。)
電影要呈現的,就是當事情的對錯涇渭分明時,整個世界卻不斷想方設法為自己的消極辯護,陷入更大的漠然,你一個人「仍能夠」堅持嗎?
你仍能讓心中銳利果敢的三角形突破冷漠的屏障,不斷地應和心中也有利尺的人們,彙集成熊熊燃燒的吶喊嗎?你能堅持相信事物仍有對錯,不捲入「恐懼已成常態」的躲避,而去判斷,去主張嗎?
事物概念或許都很僵固、簡單、沒有轉圜的餘地。但當你不斷被對側的價值覆滅、挑戰、擠壓時,仍能夠隨時堅持信念,戰勝每次微小的內心戰役嗎?電影中燃燒者突破了火焰不斷被凍結的禁錮鐐銬,就是如此微小又反覆的挑戰,也正是這微觀仍與整部電影綜觀的一致堅持,感動了我。
故事裡,真正對立的不是救火的其他異能者,或是使用火的燃燒者。這些看似分明的「水火不容」,每個人各擁固著的信念,真的無法溝通嗎?當無法愛人的惡是如此明顯,不是正逼迫人們選擇站在對的位置、可以愛更多的人的位置上?
冷調的火,熱血的救火者,當放大到更微小的單元,在愛與同理的映象單元上他們是一致的,在更大的圖示中也趨往一樣的方向,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地讓兩者轉換為同義詞:因為火刷上了溫柔與保護的淡彩,救人的手乃至心燃燒起了義憤的光,兩者不是互相滲透的迴圈(湯淺式),而是破除二元的直接轉換。
在很多世界裡,相似的故事說了許多遍,同樣的問題問了許多次。——在一百個、一千個撲滅你的對立中,你仍可以堅持自己嗎?
此時回到剛開始的問題:審視湯淺政明的作品與《普羅米亞》的區別,我想答案也應該有此一說:一個是水,一個是火。兩者看似對立,但在某種程度上又存在關係,相互依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