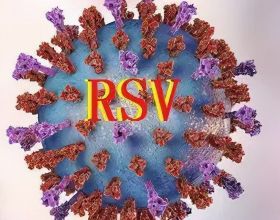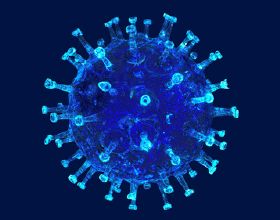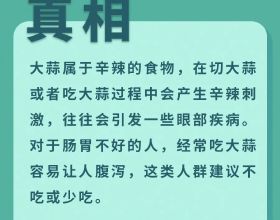作者:應福根
“長江子弟學校”是所廠辦學校,校名和長江扯不上半點關係,因為它建在鄂西的大山裡。
之所以起名為“長江子弟學校”,是因為“江河”和“長征”兩廠捱得比較近,在各自適齡學生不太飽滿的情況下,兩廠商議合作辦學,校名自然按中國人行事慣例,各家出一字,免得日後被人家誤會誰入了誰的贅。於是在看不見長江的山裡硬生生地出現了水份滿滿的“長江子弟學校”。
校內的生源也和校名一樣奇特,雖然學生們大多說的是普通話,但普通話和普通話之間差別挺大,其中東北普通話佔據絕對的優勢。
校名奇異,生源奇葩?好像應該有個說法吧。的確,上世紀七十年代關乎國家和平與發展的“三線建設”在廣袤的西南山區展開。1970年為了鞏固海防建設,一大批天南海北的“好人好馬”聽從國家的召喚,從北京、瀋陽、哈爾濱、蘭州、武漢、內蒙等國家重點工礦企業匯聚到了鄂西遠安。
為了應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敏感的邊境問題,作好打大仗的準備,三線建設工程在“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的急迫形勢下展開。
在懵懂的年紀,我和我的同學跟隨父母一夜之間遠離故土、遠離親人,走進了這個荒涼、陌生的大山裡。
剛入學,從東北來的同學看不起南方長大的同學,覺得他們瘦小枯乾不願與他們為伍;南方的來的同學覺得北方同學傻大憨粗,很少靠近他們。總之班上的同學都很彼此奇怪,彼此看不慣,彼此挑理,各種怪話層出不窮。
比如為個校名就能吵上一架。江河廠比長征廠大很多,江河子弟很不服氣,說為什麼叫“長江中學?”應該叫“江長中學”或者其它名字才對呀。長征子弟幽默地一笑,長江為什麼叫長江而不叫江長?
同在一個班聽課,日子長了慢慢地,慢慢地大家好像開始融洽了,雖然常有爭辯,但也不影響同學之間的友情。
中學時代正趕上特殊年代,上學時間有一半在學工學農學軍,就算是真正回到教室,也沒有幾個人聽講,因為“白卷英雄”成為那個時代的潮流,“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成為那個歲月的流量,而“條條道路通羅馬,老師何必硬要求,拐彎抹角不算遠,老師出題學生愁”更是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
多年後,便有了一首歌:小時候上學堂,正碰上打砸搶,十年浩劫,身心受創傷,一不會寫信二不會算賬更不會寫文章,想到如今三十多歲還是個大文盲。
那個時候,教室裡總是亂哄哄的,沒有幾個人能沉下心來聽老師苦口婆心講課,教室成了自家的自由地、後花園,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反正老師也不會管不敢管,否則扣上一頂“帽子”就一輩子廢了。
由於長得短小精悍,我常常就是坐在第一排的那一個。男女搭配,一張長方桌趴著兩個人,中間劃條“三八線”,誰也不能越界一寸,否則不是被輕薄,就是被罵“流氓”。當然,這種現象都是做給大家看的,私下裡大家還是相互來往相互交流。
很喜歡上語文課,從古到今,郭東海老師源源不斷吐出知識的芳華,讓人陶醉但卻很少同學聽課。不是不尊重老師,而是大家知道,無論學了多少知識,瞭解多少古今,早晚都是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
或許,我是唯一一個能至始至終聽完郭老師講課的人。我也想隨波逐流,但萬萬不能。郭老師每次講課都站在我跟前,好像是單獨給我開小灶,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小差。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真心喜歡上了郭老師的課。不為別的,只為他淵博的知識,只為他瘦弱的身軀裡蘊藏的巨大的能量。
郭老師不僅只是上上課那麼簡單,更多的業餘時間還在專心的寫文學作品,聽說他上大學的時候就出版過長篇小說。那個時候寫文章叫“爬格子”,要完成一篇小說或者散文,相當的費力費時,沒有一點毅力根本就無法堅持下去。郭老師寫了很多短篇小說和散文,在他抄寫不過來的時候,把一些文章交給我來抄寫,然後再投稿。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能在《○六六報》《湖北航天報》看到他的小小說或者散文。每當看到他發表的文章時,我也覺得有種成就感,暗自高興“這篇文章是我抄寫的”。
或許是受到了一種薰陶,我慢慢地喜歡上了“爬格子”。僅僅只是喜歡而已,並不奢望上報上刊。因為我知道自己的道行,也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知道我對文學有了一種特殊的情懷,郭老師很是高興,從文章的構思,到文章的開頭結尾,都沒少費功夫。
由於時代的特徵,在整個中學時代,除了語文學得馬馬虎虎外,其它各門功課都學得一塌糊塗。雖然後來也偶有文章發表,但也不認為自己是在寫文章,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寫字”,儘管字寫得十分難看。
那天,我把三江人自己寫的《三線跡憶》《口述歷史》兩本書的封面拍照發到中學群裡,想不到很多同學都希望能得到此書。可惜的是僧多粥少,實在無法一一滿足,只是找了一套給郭東海老師快遞過去。雖然無法滿足大家的需要,但也可以看出,無論時間過了多久,無論路途多麼遙遠,大家還是很懷念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結下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