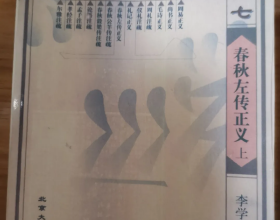□ 宣頤齋·隨筆
□ 王乾榮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真會開玩笑。先生明知自己享譽天下,誰人不識?所以故意說“不知何許人”。“閒靜少言”,也許是真的;至於“榮利”,還是有點兒“慕”嘛——您寫了詩文,作者並沒有署“無名氏”。陶令不知何處去?您署了“陶潛”“陶淵明”或“五柳先生”,還給自己“立碑”,曰《五柳先生傳》,就跟“榮利”沾邊了。
閒話表過。本人兒時讀《五柳先生傳》,百八十字,有爺爺輔導,倒是覺得不太難懂。我最讚賞其中的“好讀書,不求甚解”這個觀點,因此雖然也“好讀書”,卻不好好讀書。爺爺說:“傻小子,你往後看,‘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啥意思?”我似有所悟,但悟得沒有“不求甚解”深刻,因此養成了大而化之的毛病,伴隨終身。時至今日,老冉冉至矣,書讀了一大堆,很多時候是讀著玩兒,僅僅是把書“讀過”而已,對其全義、要義,模模糊糊,基本上“不求甚解”,管它啥意思呢。
但是爺爺的教誨,仍然不時於腦際縈繞,覺得讀書,總還要“會點兒意”的,即使不是特意“會”,其“意”無形中也在腦袋裡轉了幾道彎兒,打下了些許烙印。
我購書雜而多,每屆書市都興致勃勃抱回來感興趣的大堆書籍,但我是怎麼讀書的呢,說來慚愧……
我坦白,有些書買回來放進櫃子裡就沒怎麼翻過——當然不是絕對沒翻。它們不是辭典,但是我把它們當成了工具書。我熟悉它們的類屬,生活、工作或寫作中遇到各種難題,知道從哪本書裡查詢答案。這算一種讀書法吧。
而正襟危坐拿起書來讀,則先瞧目錄,揀喜歡的章節看,其他略去。是亦為一法。如此,我幾乎沒有把一本書從頭讀到尾的。
很多書沒有目錄,便一目十行瀏覽。感謝偉大美麗形象的漢字,目掃一片,即可知其大意。如此,偶遇精彩段落或對自己略有啟發文句,找到關鍵詞,所謂驚鴻一瞥,眼前豁然一亮,則津津有味品賞,須將它們倒背如流,也算精讀。這樣,我似乎就沒有連貫地一字一句細細讀過一本書。但讀萬卷書而撮其要者,融為一冊佳卷,略“會其意”,自娛自樂,備以用時方恨少,間或也有。此亦為一法也。
而如蕭乾和文潔若夫婦翻譯的《尤利西斯》,那麼有名,卻那麼艱澀、那麼可怕,我讀幾頁便退避三舍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細節描繪,比如寫娜塔莎家的莊園,斐然一大段,繞著圈兒說,我讀時乾脆跳了過去。
這哪兒像一個讀書人呀?答曰:咱本是三尺微命,一介草民,不算讀書人,只是打小認了幾個字,略識集腋成裘道理,養成了“讀”的習慣而已,即使蹲廁所、乘公交、等待就診……也要拿個書報之類漫讀,否則不知道在那點瑣碎的時間,腦子裡該想些什麼東西。您別說,這種零敲碎打,無心之獲,也偶有驚喜呢。
我的簡陋讀書法,只是一個平庸作者的亂彈,當然不適合從事專業性很強的人士。
錢學森說,一個真正的專業人士,專業書當精讀,跟專業相關的書應該熟讀,其他書漫讀則已。
人各有活法,書各有讀法。其實五柳先生的“不求甚解”,似乎應該理解為“不過分糾纏”,如能做到五柳先生所說,“以樂其志”,偶作閒文娛小我,足矣足矣……
來源: 法治日報——法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