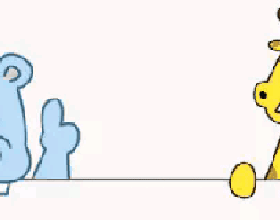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當時,廣島的監獄裡關押著一批美軍飛行員。關於他們的命運,幾十年來始終是個謎。
一張照片
B—24轟炸機的九名飛行員,在即將被派往太平洋區域作戰之前拍下了這張照片。五個人蹲在前排,機尾槍炮手還抱著一條名叫“黑子”的小狗。他們俏皮地歪戴著軍帽,飛行服上的裘皮領都豎了起來,顯得精神抖擻,信心十足。
在美國,這類攝於二次大戰的照片在人們的影集裡可以找到成千上萬,但與眾不同的是,這張照片在拍下六個月以後,照片上九個人中有五個成了戰俘死在廣島,而且是死在自己人投下的原子彈之下。
遭到厄運的還有其他美軍戰俘。此外,戰爭爆發時還有大約三千名日本血統的美國人被困在廣島,至今無人知曉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在原子彈之下。
美國官方從未公佈過死在原子彈下的美軍戰俘的人數,直到不久前,一個在新墨西哥州原子彈基地拍攝紀錄片的攝製組,意外地發現了一些有關的檔案資料,才首次揭示了事實真相。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1945年7月16日,美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試爆,於是選擇一個最佳投彈目標就成了首要問題。美軍太平洋戰略空軍司令卡爾・斯帕茨上將在給華盛頓的一封電報裡說:情報證實作為原子彈打擊目標之一的廣島,沒有關押盟軍的戰俘營。
但美國陸軍部在給斯帕茨上將的回電中卻明確指出:“完全有理由確認:在日本幾乎每一座城市中都有戰俘營。”儘管陸軍部對斯帕茨的情報持懷疑態度,但最後還是說: “‘假如’你認為你的情報確實可靠,那麼廣島就作為第一個選擇的目標吧!”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在太平洋戰略空軍參謀長柯蒂茲・裡梅設在關島的總部裡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討論投彈的細節。被挑選來執行任務的“艾諾拉・蓋伊”號轟炸機上的投擲手被召到司令部,要他在地圖上標出飛越廣島上空時選擇什麼目標投彈。這位投彈手的手指在地圖上輕輕滑過,最後指向縱橫交錯的河流上幾十座橋樑中目標最明顯的一座丁字形大橋——相生橋,這是一座廣島市民每天必經的大橋。但他卻根本不知道離大橋只有800米的地方正關押著他的美國同胞。
“孤獨女士”號
7月28日,在對停泊在廣島西南十二英里的吳港內殘存日本艦隊空襲時, “孤獨女士”號和其他兩架美機被擊落。8月2日,跳傘的飛行員全部被俘,關押在廣島西北元町區日本支那軍區總部裡。
日本和美方的記錄都證實那時至少有十名美國戰俘囚禁在廣島。目睹此事的前日本軍官也證實這些美國戰俘分別被關押在離相生橋不遠的地方。
如果說對上述情況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至少下面這些事實是很明白的。
8月6日,至少有三架美機上的十名飛行員被囚禁在廣島的三座監獄裡,大部分成員來自“孤獨女士”號,他們是在執行任務時被擊落的,其中大部分人還不到二十歲。1944年,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加入空軍,在莫洛克空軍基地受訓並編入同一個戰鬥飛行組。
訓練結束後,他們在接受了一架新的B一24轟炸機——“孤獨女士"號,並直飛夏威夷,這些青年人一路上無憂無慮,談笑風生。後來,當他們在沖繩島遊覽山洞時發現成堆的日軍士兵的白骨,才明白戰爭不是兒戲。7月27日,他們接到次日升空作戰的命令。這是他們第二次執行戰鬥任務。
指揮官告訴他們共有三十六架飛機參加空襲吳港的戰鬥。這些飛機分六次起飛,每架飛機裝載三顆重兩千磅的炸彈和副油箱,他們可能不會遇到日本戰鬥機的攔截,但高射炮火力會非常猛烈。指揮官還提醒他們萬一被擊落,要儘可能避開老百姓,向日軍投降。在接受審訊時,由於他們說不出多少對日軍有用的東西,因此以採取合作的態度為好。他們的轟炸目標是一艘排水量31000噸的“廣戶丸”號戰列艦,雖然該艦已受創,但仍可航行,它是日軍殘存艦隊的象徵,因此必須把它炸沉。
7月28日晨八時二十分,第五中隊飛機的引擎發動了。領隊圖爾克的飛機飛到中隊的最前面,後面跟著“孤獨女士”號和約瑟夫・杜賓斯基少尉的“塔洛亞”號,最後面是中隊的另外三架飛機。
四小時後,他們飛到吳港上空。在發現了那艘戰列艦的同時,地面上的日本防空部隊也發現了他們。 “廣戶丸”和海岸防空部隊一齊向他們猛烈開火,炮火密集而準確。圖爾克的飛機左翼中彈開始漏油,現在他們已飛到戰列艦的上空。圖爾克開始投彈,幾乎同時,其他飛機也開始把炸彈傾瀉下去。為了避開猛烈的炮火,中隊只得轉向西方,企圖滑過廣島,回到公海上空去。
就在這時,“塔洛亞”號被擊中。圖爾克的投彈手看見它連中三四彈,從他們的飛機下面滑向左邊,然後一頭栽了下去。“孤獨女士”號幾乎是同時中彈,高射炮火把機身掀開了一個大洞。儘管所有的滅火器都用上了,然而突然爆發的火焰卻越燒越旺。當埃利森告訴卡特賴特事情已無指望時,阿貝爾已從後炮塔那兒跳傘了。卡特賴特和其他人想等飛到公海後再跳傘,但飛機已失去控制,機艙內煙霧瀰漫。卡特賴特只好用無線電向圖爾克報告。
事後安全返航的圖爾克向上級報告說,是他命令他們跳傘的。卡特賴特最後一個跳出機艙。無人駕駛的“孤獨女士”號在空中翻了一個身,慢慢地劃了一條長長的弧形向地面栽去。
被俘
卡特賴特降落在一片叢林中,由於害怕而渾身顫抖,口渴得厲害,但未受傷。他把降落傘藏了起來,向林中的開闊地走去。這時,一個農民迎面走來。 “我馬上決定向他投降。”卡特賴特說。但每一次當他想把手槍交出時,那個農民害怕地向後縮。卡特賴特最後只好用手指了指路,於是兩人一齊走出了叢林。
十五分鐘後,他們來到一個很小的村子。這個還帶著槍的飛行員向一名村警投降,並被允許喝了一肚子水。半小時後,盧珀也被帶了進來。他顯得疲憊不堪,腿也被劃破了多處。不久,在一名村警和村民們的押送下,他們被送到一個較大的村子,眼睛蒙上黑布過了一夜。第二天他們被送上一輛卡車帶到廣島。
“我們被關進一間釘著木條的大約二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間裡,”卡特賴特說,“在那裡我見到了其他幾位飛行員。盧珀和我是最後跳傘的,所以降落點與他們距離很遠。他們比我們早一天進監獄。這些人都沒有受傷,只是垂頭喪氣,飛行服髒得一塌糊塗。”
除盧珀外,“孤獨女士"號上被俘的還有瑞安、阿特金森,埃利森、朗和尼爾(最早跳傘的阿貝爾倖存下來,後來回到了美國,彼德森和領航員的屍體一直未找到)。牢房裡還關著兩名海軍航空兵飛行員和幾名日本囚犯。他們都坐在地板上,彼此之間不準交談。日本警衛透過木柵監視著他們。夜裡,他們用發來的破爛毛毯裹著身子,蜷縮在地板上。一隻小桶用來大小便,什麼也沒有給他們吃,頭頂上的一盎電燈始終亮著,警衛一步也不離開。
在不遠處的憲兵司令部裡,同時關押著“塔洛亞”號上的兩名飛行員。他們是在飛機墜毀前五個跳傘者中的兩個。
杜賓斯基在飛機離地面很近時才跳傘,結果因傘未及時開啟摔死了;機械師皮斯科降落在一座種植園的房頂上,不料被老百姓抓住摔下房,當場死去;報務員布什菲爾降落在太田河的港灣中,也被漁民拖上岸來打死,而其餘的六個人在飛機撞上一座小山時全部死去。
“塔洛亞"號上的兩名倖存者鮑姆迦納特和莫爾納都降落在離他們飛機墜毀處不遠的稻田裡,德老百姓趕來之前被憲兵抓住。他們不知道離關押他們大約450米的地方還關押著七名“孤獨文士”號的飛行員,在日本人手裡和他們共同度過這一夜。
那天夜裡,在廣島另一座監獄裡至少還關押著另外兩名美國海軍航空兵飛行員:一個是少尉駕駛員波特,另一名是報務員羅蘭·布里斯特。他們是在7月28日早晨轟炸吳港地區另一艘日本重型巡洋艦時被擊落的。他們掉在日本海里,隨後爬上了一條橡皮艇,可是不久就成了俘虜。
7月30日早晨,卡特賴特被兩名日本警衛弄醒,帶到一間審訊室裡。一名日軍軍官和一名翻譯對他連續審訊了幾小時。起先問得很隨便,後來由於卡特賴特的不合作態度,那名軍官就動手揍他。他由於前一天喝了大量生水而嘔吐起來,立刻被帶到大樓外面的廁所裡去,當矇眼的黑布取下時,卡特賴特從小小的窗戶和門縫望去,“河流、橋樑和這座大樓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了。”
第二天審訊變得更加嚴厲了。卡特賴特被警告說:如果再不採取合作的態度,就要把他交給更加嚴酷的對手。不久,他就和同房的兩名海軍飛行員被送到火車站,塞進車廂送到東京受審,然後將蒞橫濱槍斃。在押走的時候,卡特賴特認為那些默默地坐在牢房裡的夥伴至少要比他“稍稍幸運些。”然而想不到四個星期後,在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之前,他就獲得釋放。
原子彈下的廣島
8月6日早晨的廣島顯得那麼炎熱、潮溼。八時十五分, “艾諾拉・蓋伊"號的機組人員從三萬一千六百英尺的高空向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不到一分鐘,在離他們的投擲目標——相生橋只有243米處發生了猛烈的爆炸,升起了高達一千八百九十英尺蘑菇雲。
衝擊波向四面八方擴充套件,一團直徑為六百五十英尺的大火球在一瞬間燒焦了大地。一英里範圍內所有的高層建築都被摧毀;木結構房屋被震得支離破碎。離爆炸中心只有500米遠的廣島醫院轉瞬之間成了一堆瓦礫。95%以上的人當場死去,離爆炸中心1000米遠的人也有75%死去,還有20%以上的人受傷。
三十分鐘後大火全面燃起,灼熱的風時速高達四十英里,隨後下起了一場粘乎乎的帶有放射性物質的黑雨,天氣突然變得寒冷刺骨。雨一直斷斷續續地下到下午四點。到這時已有8000多人喪命,12000多人在死亡線上掙扎。廣島醫院周圍一英里半之內的一切都成了灰燼。
整個元町區一片混亂。第二天,一個親眼看到那些美國士兵的外科醫生對他的同事說:“他們的眼睛、鼻子和嘴被火燒得看不清了。你無法說出他們的後背和前胸有什麼區別。一個被燒得只露出一排白牙齒的美國兵向我討水喝,但我沒有一滴水,只能合掌為他祈禱。他再也沒有作聲,大約這就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請求吧!”這段見聞後來刊登在一家日本報紙上。
囚禁“塔洛亞”號飛行員的日本憲兵司令部離爆炮中心只有450米左右,已被夷為平地。
而囚禁“孤獨女士”號飛行員的支那軍區司令部離爆炸中心有800米遠。這座司令部大樓是石頭水泥結構,雖然發生倒塌,但沒有被大火吞噬掉,只是大樓兩側木結構的廂房被燒得蕩然無存了。因此關在主樓裡的幾個美軍戰俘有可能死裡逃生。事實也是如此。那時至少有三人還活著。他們是報務員羅蘭、一名海軍飛行員和尼爾。有人看見這三個人一點也沒有受傷。
親眼看見這三個還活著的是另外十名美國飛行員。他們是在原子彈爆炸兩天之後駕著B一29轟炸機從提尼安島起飛去廣島,但在半途遭到高射炮火攔截而被擊落的。他們在日本海漂浮了六天。十天後被帶到原子彈劫後的廣島,關押在離廣島火車站不遠的一個掩蔽部內。他們用美國香菸跟一個會說英語的日軍衛兵換飯吃。
就在他們啃著米飯糰的時候,外面一陣騷動,隨後兩名身穿飛行服的美國人被帶了進來。“他們的樣子真可怕,”後來住在馬薩諸塞州的副駕駛員霍爾登說,“我們和他倆交談起來。他們說原子彈爆炸時城裡還關著其他美國人,有的當場死去,他倆爬進了一座汙水池才倖免於難。汙水一直淹到他們的下巴,原子彈燃起的大火在熊熊燃燒,灼熱不堪。火勢減弱以後,他們馬上爬出汙水池,但立刻被日本人抓住。這兩個人真是死裡逃生,看看他們的樣子就明白了。他們不斷地嘔吐,身上到處是青紫的傷痕。我們B一29轟炸機的飛行員們整夜不停地安慰和看護他們。”
第二天,一個名叫福井的日軍少尉走進掩體用英語告訴他們。一些日軍軍官想把他們殺掉,但他要設法幫他們逃出虎口。那天是8月17日,兩天前天皇已向國民宣佈目本戰敗,廣島日軍的軍紀已土崩瓦解。
福井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受美國傳教士的影響頗深。那天晚上五點,他弄來一輛卡車,準備把他們送到憲兵司令部去。“我們上了卡車,”羅斯說,“他把卡車停了下來,除去蒙在我們眼睛上的黑布,要我們全體起立站在卡車上看看廣島。我們看不見任何豎立的東西,到處是廢墟,街上空無一人,死一般地沉寂。”
“我命令司機停車,”福井後來說,“命令那些飛行員好好看看那些藍色的火焰。我告訴他們那是在焚燒婦女和孩子們的屍體。"他還說:“看焚燒孩子大概是很有趣的事情吧?美軍在廣島丟下那顆可怕的炸彈,真是喪盡天良!”
二十分鐘後,他們來到憲兵司令部,獲許洗滌、吃飯,然後被關進一間小牢房過夜。羅斯和霍爾登再也沒有見到那兩名泡在汙水池中的飛行員。第二天,他們獲悉尼爾傷重已死去,羅蘭也病得很厲害,後來成為死在廣島的最後一戰俘。在一名B一29轟炸機飛行員被送到另一座軍營準備遣返美國時,這兩名死去的飛行員就地被掩埋了。
1945年12月6日,日本投降後的第十三個星期,也是這兩名飛行員死後的第十五個星期,美軍3064埋葬營部隊的約翰·戴在廣島把他們的屍體挖掘出來。一星期之前,約翰·戴還在離“塔洛亞”號墜毀不遠處挖出了杜賓斯基和其他六名飛行員的屍體,兩名被日本老百姓打死的飛行員的屍體也被掘了出來。另外還發現了二十多具美軍人員的屍體,而這些人的姓名卻永遠無法知道了。
在日本人中間流傳著各種各樣有關美軍戰俘在廣島受到原子彈襲擊時的故事。說得最多的是,“一個長著金髮碧眼、面板自晰的漂亮男孩”被綁在一根柱子上,身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道:“你走過以前,先揍這個美國佬一頓。”最後他被人用石塊和棍棒活活打死,就死在“艾諾拉·蓋伊”號所選擇的作為投彈目標的相生橋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