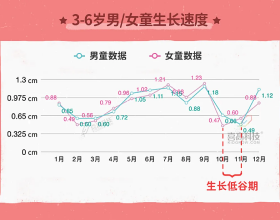“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昇……”
兒子學唱兒歌時,昂頭問我:爸,太陽不是從東方升起嗎,幹嘛說從北京升起啊?天安門是在東海嗎?
兒子天真的問話,讓我不由得想起風靡家鄉的幾句調侃:國宴都是羊肉湯,舉國都說剛剛剛;臨朐土話成國寶,首都遷到沂山上。
兒子天真,家鄉的父老鄉親可親可敬。首都,那是自明代建都,是舉國仰慕的地方,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能遷來遷去嗎?
正因為北京位置的不可替代性,便如眾星捧月般具有磁力。如此說來,想把首都搬遷到家鄉的沂山之巔,豈不是白日夢?答案是肯定的。臨朐人民不幼稚,是盼望北京人民來沂蒙山區呼吸新鮮空氣,來旅遊觀光。
絮叨了半天,還沒貼著正題。我想說的,是進京城的記憶點滴。
因為早年分管機關,經常陪頭兒去北京聯絡工作。作為最低基層的院,去最高的衙門聯絡什麼呢。彙報請示?不是,還隔著省市領導呢。是走親戚?俺們的親戚都是老實巴腳的鄉下人。去北京,都是為了爭取上級領導的支援,說白了,是爭取扶持。
打小看北京風光圖,便知道,除卻天安門外,還有諸如北京飯店、釣魚臺國賓館等景點。初次進京,頭兒禮賢下士,徵詢我等部下說,進京了,想住在哪兒?“住北京飯店”,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振臂高呼。為什麼呢?頭兒問我了。我說,來北京就得住北京飯店,在我們臨朐就住臨朐大酒店,開開眼界嗎。你帶著多少銀子?頭兒問我。“足足五十張老人頭呢”。我心裡底氣十足,反正臨走時把財務上的現金全帶上了,縣城最高檔次的大酒店每晚住宿也不過幾十元,你北京飯店還能超過二三百元?嗨,你帶的現金,還不夠北京飯店的一頓飯錢呢,還想住宿,沒門。頭兒的話,嚇得我等連連吐舌頭。北京啊,你真是牛!
跟我來吧,咱去住紅太陽昇起的地方。一陣興奮,一陣眩暈,看來是要住進紫禁城了。頭兒好大方!這車轉來拐去,總是圍著天安門廣場轉悠,但就是不進紫禁城。迷糊間,頭兒叫下車。轉轉悠悠間,鑽進了一條小衚衕,接著擠進了一個火柴盒般大小的院落。這是哪兒啊?北京竟然有這般小家子氣的地方?頭兒吁了一聲,指著門牌不做聲。“最高人民**院招待所”,哇塞!高院的招待所設在這牆角旮旯裡啊。真是小家子氣十足。這座兩層小樓還能盛下高院的大人物?
當我遞上工作證,高院招待所服務室的美女很客氣(自我感覺吧)說,臨駒(該稱臨朐,北京也有文盲,真不該!)是哪個省的?山東的!為顯山東大漢的豪爽,我故意把嗓門提高了八度。美女在我的震駭下,說,標準間全滿了,只有豪華間了,不過這豪華間都在地下室。一說豪華間,我就發毛,不會是頭兒說的幾百元一晚上吧?當湊前一看,心裡樂了,每晚19.7元,其中的0.7元還是保險費,真比老家飯店幾十人一間的通鋪還便宜呢。住下,拍板沒商量。
地下室,在老家曾聽說過,是窖藏地瓜的所在,冬暖夏涼的好地方,但住人還是頭一回聽說。當開啟地下室的門,嗬,小小空間,擠著四張小鐵床,暖和還可以,可很悶的,很不舒服的感覺。當然,這樣廉價的房價,住北京飯店是牆上掛畫——沒門的。最最要命的是沒有洗手間。作為年輕人的我還湊付,內急了,披上棉衣爬上二樓找洗手間。可是對年過不惑的頭兒他,上躥下跳,不是戲弄他嗎?於是乎,求情再三,給頭兒安排了地上一樓的單間,我跟司機住了地下室,體驗生活嗎,打小還沒住過窖藏地瓜的地窨子呢。今天來北京,就體驗下作為地瓜的身份吧。
於是乎,十幾年如一日。進京就住高院招待所,進所就鑽地下室。習慣了,便有了老鼠鑽洞的感覺,甚至停電了,還能目光如炬,一覽無餘。差點趕上偵察兵的眼力了。
再後來,陪後來的領匯入住招待所。新頭兒說,這兒有什麼魅力讓你一頭就扎進來?隔著天安門近啊,看升旗,逛廣場,望城樓,舉手之勞。
新領導說,高,高招!後來一想,新領導是褒還是貶?心一橫,不管這麼多了,離著天安門近,觀光不用買門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