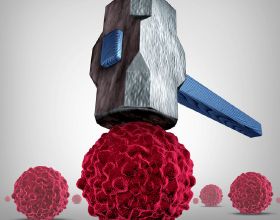無國界醫生自述:並肩工作的阿富汗同事,被美軍炸死了
趙一凡 42 歲,曾是無國界醫生的一名麻醉科醫生,2013 年他前往阿富汗昆都士創傷醫院,為病人提供無差別救助。1971 年,無國界醫生在法國巴黎成立,是個獨立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他們全球範圍招募醫生和其他專業救援人員,派遣到深受武裝衝突、流行病和天災影響的地區,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援助,無論這些病人的種族、宗教、或者政治立場是什麼。
-1-「天涯俠醫」
我居住在廣州,是一名從業 19 年的麻醉科醫生。2012 年的時候,我剛剛晉升成為一所三甲醫院的副主任醫師,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也都在不斷地重複。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拓展自己的事業,做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偶然間,我看到了一部香港電視劇,叫《天涯俠醫》,講的是無國界醫生的故事,看完以後覺得很受觸動,於是自然而然地,就開始在網上搜索無國界醫生的相關資訊,後來發現他們對麻醉科醫生的需求還蠻大的,就報考了。在太太的鼓勵和支援下,我通過了無國界醫生的筆試和麵試,被順利錄取了。人事部的工作人員跟我商量目的地,我說想去一個蚊子少一點的地方,於是他們把我派到了阿富汗。
■ 《天涯俠醫》劇照
-2-喀布林的 AK47 與裝甲車
2013 年 4 月,我乘飛機到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林。在喀布林機場的海關,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警察,每個人都端著一把 AK47。過了海關之後,機場大廳裡突然湧現了一幫穿著制服的人,他們並不是什麼工作人員,而是靠拎行李賺小費的人,一見我是外國人,就一擁而上地圍住我,爭先恐後地要幫我提行李。我當時還挺緊張的,只顧著緊緊攥住自己的行李,埋頭向前走。後來出了機場,找到接我的人,我才順利地抵達了無國界醫生在喀布林的辦事處。有人把我帶到一個小門,向我示意馬路對面餐廳的位置,表示我可以先出去吃個飯。於是我第一次一個人真真切切地走在了阿富汗的街道上,馬路顯得破舊且直白,沒有任何雙黃線和訊號燈,四方形的房子矮小且破敗,但好在都還堅固完整。我直徑向餐廳走去,轉眼就瞥見右手邊停靠著一輛裝甲車,車上幾個人都端著槍談笑風生。我暗自「哎呦」一聲,心想這回可真是長了見識。
■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林街頭 Andrea Bruce/Noor Images
-3-饢和健怡可樂
在喀布林短暫停留之後,我就啟程去了阿富汗北部山區的昆都士,接下來的幾個月,我一直在那裡的創傷醫院開展無國界醫生的工作。昆都士創傷醫院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麼野生,至少是正常的建築,而不是紮在野地裡的帳篷。醫院裡共有兩間手術室,裝置很簡陋,只有一個分體式空調,使用紫外線消毒,如果覺得空氣不好就直接開啟窗戶通風(在國內的醫院裡,基本都是層流手術室)。而手術使用的麻醉監護儀和麻醉劑,我相信,是我老師的老師都沒有使用過的「古老」品種。等到我參觀完醫院、聽完同事的介紹,已經過了飯點了。一位叫艾斯曼尼的本地醫生熱心地給我買了一個饢和一瓶健怡可樂——是一個看起來挺奇特的套餐,但當時我已經餓得不行了,只顧著一頓狼吞虎嚥。之後,我想要把飯錢還給他,他執意不收,這位穿著西裝領帶、踩著皮涼鞋的本地青年,朝我擺擺手,自豪地說「這是阿富汗,你儘管吃就好,不用給我錢!」
■ 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 MSF/Ben King
■ 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一名當地婦女走在醫院附近的路上 Michael Goldfarb/MSF
-4-受傷的婦女
我到創傷醫院的第一天晚上,就接手了第一位病人,是一名本地婦女,腰部槍傷,子彈打破了她的腎臟。我為她實施了全身麻醉,她被推進手術室,進行了剖腹探查和腎切除的手術。手術順利完成,這位太太醒過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手術做了嗎?」我當時聽了心裡很高興,她在手術中沒有任何感覺,說明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麻醉。其實麻醉科醫生的工作不只是打一針麻醉這麼簡單,我們的任務是保證病人平安舒適地度過整個手術期,包括術前評估、制定麻醉方案、關注術後注意事項等等。
■ 趙一凡為準備手術的病人實施麻醉,在阿富汗的兩個月時間裡,他和同事完成了五百臺手術 趙一凡
作為無國界醫生,我們通常不太會過於執著地詢問槍傷的原因,因為很多時候病人受傷的原因可能非常敏感。包括這位腎臟受傷的太太,她只是告訴我們,「這一槍是我自己不小心打的。」這是我感受到的非常大的一個文化衝突——阿富汗是一個絕對男性主導的國家,女性沒有受教育的權利(2001年前),凡事都要聽從於男性,甚至在受到傷害的時候,都不太敢說出始作俑者。還有一點印象深刻的是,幾乎我們收治的每一位創傷女病人,都是懷著孕的,好像她們唯一的職能就是生孩子。因為每個家庭都會生很多孩子,當地家長並不會把孩子(尤其是女孩)看得像國內這麼重要。孩子們平時在外面玩,到飯點了就回家吃飯。在這樣的情況下,孩子受傷的情況也非常多。比如,哥哥在耕地,妹妹突然跑到哥哥面前,一個沒注意,妹妹的腳趾頭就被鋤頭剁掉了。
■ 無國界醫生的外科醫生為一名男孩問診,這名小男孩在車禍中斷了一條腿 Michael Goldfarb/MSF
■ 一名婦女抱著孩子來到昆都士創傷醫院的急診室 Michael Goldfarb/MSF
-5-巴斯敏娜
對於麻醉醫生來說,能記住的往往是那些傷情比較嚴重、需要反覆接受手術的病人。對於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名叫巴斯敏娜的小女孩。她大概八九歲的樣子,長得瘦瘦小小的,她原本跟著爸爸媽媽參加一場婚宴,沒料想婚宴上兩幫人突然開始槍戰,子彈像刀子一般割開了她的腹部,胃腸道受到了致命的傷害。我們當時馬上為她做了剖腹探查、清創、縫合等等。第一次手術很順利,第二天早上她的精神狀態已經很好了,躺著床上看漫畫書,吃了香蕉和酸奶,我們看了都很高興。但沒想到的是,她發生了腸瘻和腹膜炎,腸道的傷口始終沒有長好,吃進去的食物會從傷口裡漏出來。因為當地醫院沒有任何靜脈營養,小女孩只能透過吃東西來獲得營養,病情就陷入了一個惡性迴圈。每次手術前後,我會與巴斯敏娜的爸爸做一些簡短的交流。跟阿富汗的大多數爸爸不一樣,他是真的非常愛自己的女兒,他跟我歲數差不多大,但是臉上的皺紋很深,看起來更蒼老一些。我也有一個女兒,所以格外能理解這位爸爸的擔憂和心痛。在最後一次手術之前,我安慰他說,「我們會竭盡所能救治你的女兒。」可是那次手術沒能挽救小女孩的生命,腸瘻始終沒有好轉,她最後幾乎是被餓死的。這件事對她爸爸的打擊很大,我看見他一直在哭。
■ 一名 12 歲的女孩在事故中受傷,在無國界醫生昆都士創傷醫院接受外固定手術 Camille Gillardeau/MSF
■ 在昆都士創傷醫院的門診部候診的病人 Mikhail Galustov
-6-「Doctor! Doctor!」
從上世紀末開始,阿富汗的局勢始終非常不穩定。80 年代有蘇聯入侵,90 年代有塔利班興起,911 事件後有美國的進入。我所在的昆都士地處阿富汗北部的山區,當地也潛伏著一部分塔利班勢力,偶爾會爆發小規模的武裝衝突。我本人倒是沒有親眼見到過正面武裝衝突,但是偶爾會聽到一些零星的爆炸聲。出於安全的考慮,我們不可以上街行走,每天只能兩點一線地往返於醫院和宿舍之間,不可以拿著相機隨意拍照,住處的窗戶外面也有一層布作為遮擋。不過在離開之前,我申請到了一次機會,可以走上昆都士的街頭,逛一逛當地的市集。當時跟我們同去的還有一位導遊和兩位保安,一路上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在這個街角誰中過槍、在那個街口誰被暗殺了……但是當我們到了市集,我突然驚喜地發現當地的老百姓在對我們夾道歡迎——他們都自發地站在路邊,用不熟練的英語叫著「Doctor! Doctor!」微笑著看著我們。那個時候我真的好高興,頭一回發現原來在這裡醫生可以這麼受尊重,這跟國內的醫患關係很不一樣。
■ 昆都士街頭的當地藥房 Mikhail Galustov
■ 在宿舍內,趙一凡和所有國際救援人員合影 趙一凡
-7-回到廣州
六月中旬,我結束了在昆都士創傷醫院的任務,回到了廣州。我記得剛剛回到家的那一個星期,一連七天,每天晚上睡覺我都能夢見自己在處理各種各樣的創傷病人,就好像自己從來沒有離開一樣。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地一直在摸我太太的肚子,我夢見創傷醫院裡來了一位急診病人,我要摸摸他的肚子是軟是硬,有沒有板狀腹、腹膜炎的情況。結果我太太把我拍醒了,問我在幹嘛,我猛地睜開眼睛,發現周圍一片漆黑,才發現原來我已經在廣州了。回到廣州兩年後,2015 年 10 月 3 日,我突然得知之前工作所在的昆都士創傷醫院在持續轟炸中被數次擊中,造成 42 人死亡,之前請我吃過饢和健怡可樂的本地醫生艾斯曼尼也不幸遇難。聽說他原本已經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始終堅持在創傷醫院兼職,那天晚上他是回來頂班的,空襲發生時他還一直守著他的病人。後來我反覆提起他的名字,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這樣一位在戰亂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他很熱愛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職業,他始終堅持在救援的第一線。我覺得他是真正的英雄。
- 採編:王王王誠圻
- 部分文案:趙一凡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