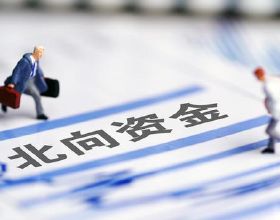自兩千多年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我國的思想文化統治一直都以儒家為主;然而該現狀卻並不適用於嶺南地區,因為嶺南儒學的實際普及歷史僅一千年左右,這在某些人口中便有了“文化沙漠”的口實。
“沙漠”一說並不可怕,沙漠也可成綠洲,可怕的是某些人“選擇性失明”、直接忽視了嶺南儒學在明代時“後來者居上”的史實,始終將嶺南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文化圈之外,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局地文化、代表不了中國,歷史現實是否也如此呢?
談及這話題,就不得不要了解儒家“理學與心學”的分水嶺,而這分水嶺正源自明代的嶺南。
明代之前的嶺南儒學
雖說秦漢時期已實現了嶺南與中原地區的大一統,但直到唐代之前、嶺南士人在我國曆史上始終只是“星星點點”難以燎原,其根源正因儒學教化長期得不到普及、文化教育未能蔚然成風。
漢代時的嶺南說是“文化沙漠”並不誇張,越族文化、俚寮文化一直佔據主流,而且長期來動盪頗多、到冼夫人家族(馮氏家族)令“嶺表大定”時已是唐代初期了。我國大一統王朝的歷史上,第一位嶺南籍封疆大吏是唐貞觀年間的馮盎將軍,正是他這家族帶領嶺南百姓安然度過了南朝至隋唐近二百年的戰亂。
在廣東人心目中,第一位出現在中國王朝歷史上的儒家文人是韶關人張九齡,他固然是因為熟讀諸子百家而晉身朝堂、不過其首要身份卻是“大庾嶺路開拓者”、“名相、政治家”,然後才是“文學家、詩人”。
由於工作關係,開闢了大庾嶺路的張九齡並未能對嶺南儒學及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貢獻,初步做到這一點的、則是唐代中期貶謫嶺南的韓愈。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韓愈,韓愈在嶺南播下的是名副其實的儒學“火種”,所以“嶺南先賢”名單裡韓愈佔其一當之無愧。
韓愈:嶺南儒學的實際播種者
後來宋朝的蘇軾又在廣東加柴添薪,嶺南“儒風”這才徐徐漸起,可惜南宋末年時又在新會崖山壯烈地為南宋王朝集體殉了葬。在整個宋朝當中,融合佛、儒、道一體的“宋代理學”(程朱理學)成為了儒學自漢代以來的一個頂點、但同時也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死氣沉沉的教條主義僵局,宋亡之後、中原南北內外的漢儒文化一時間便“波瀾不驚”了!
當代部分學者認為、明朝時振興儒家思想的是“陸王心學”,因為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的思想……這當中的說法就明顯跳過了嶺南儒學在這關鍵節點上的巨大貢獻。
為何這麼說呢?看看明朝初年時思想界死水一潭的局面便知;然而打破該僵局的關鍵歷史人物則被“某些人”選擇性忽略(在歷史教材上從未存在過),直到如今、國人對其人其事依舊談不上很瞭解。
明代儒學的“綠洲”與分水嶺
正如上文所述,明朝初年時佔據主流意識形態的依舊是宋亡以來的程朱理學,陸九淵實際上並未翻起多大的風波來。
明代儒學歷史中,真正打破程朱僵局、開啟心學歷程的人是嶺南教育家陳獻章(1428~1500年,廣東新會人),當陳獻章桃李滿天下之時、更為人所熟悉的王陽明尚處於人生的迷惘當中,所謂的“龍場悟道”也是他偶遇陳獻章的學生湛若水之後才發生的。
在陳獻章建立“江門學派”的年代,明代朝廷樞要裡大量要員均是其學生、嶺南士人也多受其影響,儒學文化一度蔚然蓬勃、成為了儒學死氣沉沉時代裡的一抹“綠洲”。
當時,番禺沙灣的何氏、南海九江的朱氏均為嶺南的儒學望族,家族中泰斗者多有陳獻章的高足,增城湛若水的“甘泉學派”更是直接源於陳獻章學說。今人進入番禺沙灣的何氏祖祠,尚可見到陳獻章親書的“留耕堂”及“詩書世澤”等聯匾、參觀南海朱次琦(九江學派)的儒學淵源時,同樣可追溯到陳獻章的“江門學派”。
在廣東省博物館的古代文化篇章裡,關於嶺南儒學首列的前三人便是陳獻章(明)、屈大均(明末清初)、朱次琦(清),他們代表的正是嶺南儒學一脈相承的前後關係,也是當代儒學發揚光大的真正基礎。
這三人當中,如果說陳獻章奠定了嶺南儒學的“綠洲”,屈大均則是明末清初儒家思想的碩果僅存者(當時更多的著名儒家士人則跟宋亡時一樣、轟轟烈烈地葬身在反清復明鬥爭當中了),而朱次琦作為康有為的老師、康有為又作為梁啟超的老師,直接開啟了嶺南儒學在當代“承前啟後”的局面。
明末著名學者黃宗羲(著有論述明代心學的《明儒學案》)在論及當世儒學體系時就曾質疑:“有明之學,至白沙(陳獻章)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
當代教育家馮友蘭也同樣質疑:“白沙卒於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時王陽明二十餘歲;甘泉卒於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與陽明時相辯論。陽明之學,雖亦自得,然亦必受此二人之影響也。”
可見,對只提“陸王心學”而越過嶺南儒學,這樣的“選擇性失明”還是有頗多有識之士察覺到並曾為之鳴不平的,我個人也據此對王守仁的人品頗有質疑。
當代儒家文化實際上均是“南派儒學”
當代改革開放之後,無數學者痛心今人“道德淪喪”、開始重新倡導儒家思想裡的部分精華學說,世界各地也興起了“孔子學院”。
所謂“精華”,實際上是儒家自孔孟(漢唐)、程朱(宋代)之後的“明代心學”,這套學說一直備受許多世界偉人推崇,也是當代人所接觸的儒學“最新版本”。
明代二百七十餘年曆史中昭準從祀於曲阜孔廟裡的僅四人(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當中的陳獻章與王守仁不分先後並列,昭示著心學”後來者居上“的超然地位。而透過明代心學的歷史我們不難得出、心學實際上就代表著”嶺南儒學“,王陽明的貢獻則是將其發揚光大並推廣到了全國以至於全世界,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它不是嶺南文化裡的一部分。
梁啟超在談論民主思想的“北伐”時也曾說過,早在唐代和明代、惠能(南禪宗)以及白沙先生(儒家心學)就曾成功實現了嶺南文化的兩次“北伐”,如今的“第三次”也是歷史必然趨勢。
無論明代心學是稱“陳湛心學”還是“陽明心學”,它都是宋明儒學的分水嶺、也是當代儒家文化的實際載體。自宋朝在嶺南地區覆亡之後、傳統的中原思想文化已發生了實際上的整體“南遷”,再加上明代心學在嶺南地區的崛起,這樣的”後來者居上“早已成了儒家思想歷史程序的一部分,只是這樣的變化一直未廣為人知,“陳獻章、湛若水、屈大均、朱次琦”等對大多數國人來說還是偏陌生的名字。
在我國南方各地(嶺南、閩浙、江南),宗祠文化隨著儒家的禮義仁孝思想深入人心,而嶺南地區大量漂洋過海的人們又將這樣的優秀傳統帶到了海外,這些源自儒學的文化一度成為代表“中國人”的優秀內涵之一......而反觀如今的中原腹地,宗祠今還安在?禮義仁孝是否尚在骨子裡?過去的“謙謙君子之風”怕是早已成了追憶。
相關話題有傷和諧、我在這裡就不便開啟了。套用廣東許多出租車、網約車司機的話說:“如果乘客是廣府一帶的人,行程多半會是美妙和諧的;如果乘客來自內地,我們就得做好銖鎦必究、被投訴等各種心理準備了”,到底什麼原因令他們產生這樣的說法,這真的值得我們深思!
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本號將堅持文章100%原創(部分圖片來源網路,若存疑義聯絡即刪),持續為大家輸出選題豐富的文化史論內容;文字均親自碼出,觀點為個人見解,絕無任何對映行為,歡迎訂閱轉發及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