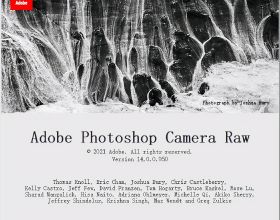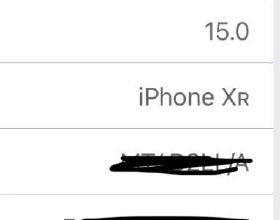生命的顏色
跟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槍是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特有的主題。
近半個多世紀,槍成為美國宗教、政治和文化保守派的象徵符號,也是共和黨候選人團結選民的一面鮮明旗幟。反對政府控制槍支的保守選民有效地把選舉變成對《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公投,形成共和黨最穩固的基本盤。任何共和黨候選人要贏得選舉,必須獲得這個群體的支援。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里斯市一位名叫喬治·弗洛伊德的黑人在警察粗暴執法過程中死亡,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全國性抗議。一些城市的抗議演化成暴力事件。進入夏天,新冠疫情和抗議活動隨時可以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影響不同群體選民的選票投向。每天公佈的感染人數、死亡人數、街頭的火光和槍聲、特朗普總統火上澆油的言行,相互疊加,不斷衝擊民眾的感受,激發民眾的情緒。休謨說,理性是激情的奴僕。在驅動人的行為方面,情感往往比理性更直接、更強烈。
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克諾沙市一名黑人拒捕,警察從背後開了七槍,其中四槍擊中,重傷送醫院。有關事件的具體細節,事後各方描述不同,警察的行為是否正當或是否涉嫌違法,州和聯邦執法部門還在調查。事發當天,有人把槍擊的錄影貼到社交媒體,迅速傳播,引發大規模抗議。當時,正值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全國性抗議逐漸平息之際,抗議的火焰突然重新燃燒起來。克諾沙成了抗議的新震源;示威抗議迅速演化成騷亂。
一位17歲的少年成為克諾沙騷亂的焦點。凱爾·裡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高中輟學,跟母親生活,住在伊利諾伊州北端的小鎮安提阿。從安提阿向北兩公里就是威斯康星,跨過州界向東北方向走30英里就是當地最大城市克諾沙。像很多小鎮少年一樣,凱爾喜歡進城玩耍,在克諾沙街頭留下很多印記。騷亂髮生前一個月,有路人看到幾個年輕人在街頭打架,其中就有凱爾。他從背後用拳頭擊打一位不知名的女子。騷亂前一週,克諾沙政府控告凱爾無照駕駛,超速20英里。凱爾從小熱愛槍支,想當警察,14歲時參加了一個本地警察局的青少年學員專案,坐警車觀看警察執法,學習使用槍械。近幾年,民眾中流傳一個支援警察的口號“藍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凱爾在臉書曾反覆張貼這個口號。“藍”是代表警察的顏色。
2013年,美國興起“黑人生命,不容踐踏”(Black Lives Matter,一譯“黑命也是命”)運動,抗議針對黑人的執法暴力。2014年12月20日,兩名紐約市警察在警車中被一名黑人歹徒槍殺,其中包括32歲的華人警察劉文健。遇害時,劉文健才新婚兩個月。兩位紐約警察的被害引起全國執法人員的憤怒,有執法人員組織提出“藍命也是命”,要求聯邦政府立法,把針對執法人員的犯罪也列入仇恨犯罪。
“黑命也是命”、“藍命也是命”,還有後來的“白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像幾枚稜鏡,折射出美國社會相互交錯的種族、左右、階層矛盾。一些個人的病態和偶然的人生錯誤,漸漸被泛政治化了。極端事件醞釀極端政治。紐約警察被害引起全國執法人員憤怒,明尼阿波里斯和克諾沙黑人被害引發全國黑人的憤怒。憤怒的人群是極端政治的溫床。
疫情救濟款
雖然凱爾高中輟學,加入警察隊伍的前景渺茫,但從不掩飾對警察工作的熱愛,喜歡告訴別人自己是民兵(但沒有民兵組織承認他是自己的成員)。隨著年齡的增長,凱爾表現出巨大的政治熱情。2020年1月30日,凱爾剛過17歲生日,趕赴400英里外愛荷華州的得梅因市參加特朗普的集會,站在臺下第一排。凱爾有著特朗普堅定支持者的典型特徵:白人男性、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愛好槍支、相信“藍命也是命”跟“黑命也是命”勢不兩立。
凱爾有個年長他兩歲的姐姐,兩人隨母親生活。他母親單身,在一家老人院做護士助理,收入微薄,供養一子一女,生活不易,兩年前曾申請破產。他和姐姐上初中時遭到同學霸凌騷擾,被罵又蠢又傻。他母親求助警方,要求保護兩個孩子。凱爾15歲時從高中輟學。
2020年3月,疫情蔓延,美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3月27日,特朗普總統簽署2.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救濟陷入困境的公司和個人。4月初,財政部開始向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的國民寄發支票,成年國民每人1200美元,17歲以下的國民每人500美元。聯邦政府同時向疫情中的失業人員增發每週600美元補助。凱爾生於2003年1月,剛滿17歲,收到1200美元疫情補助。疫情前,他在“基督教青年會”做業餘救生員;疫情中失業,又從聯邦政府得到每週600美元的失業補助。這比他在“基督教青年會”打零工的收入還高。
凱爾有了餘錢,想購置的第一個大件就是槍。但在威斯康星州,法律不允許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購買槍支。當時,凱爾的姐姐正跟多米尼克·布萊克(Dominick Black)約會。多米尼克比凱爾大兩歲,可以合法買槍。凱爾求他幫忙,把錢給他,請他代買。像凱爾一樣,多米尼克也是跟母親生活,母子住在克諾沙。多米尼克為凱爾買了一支斯密斯·威森AR-15半自動步槍,存放在繼父家中。他告訴凱爾,等到狩獵季節,可以一起帶著去北部打獵。按照威斯康星法律,18歲以下未成年人只有在打獵時可以帶槍。
克諾沙騷亂中,一些沿街店鋪遭搶劫,汽車被燒燬。市政府宣佈宵禁,州政府派遣執法人員協助本地警察維持秩序。同時,有民眾開始帶槍向發生騷亂的城區聚集。8月25日早晨,多米尼克開車帶凱爾到他繼父家取走AR-15步槍,趕赴城區。路上,多米尼克給繼父打電話,說他要去城裡幫助清洗示威者留下的塗鴉,並替以前打工的車店保護財產。繼父告訴他,最好別去。多米尼克沒有聽從繼父的勸告。他帶凱爾去了一家汽車維修店,各自武裝起來,幫助看守生意。現場來了一些他們不認識的民間武裝人員,說是響應臉書上一個叫“克諾沙衛兵”組織的號召,來保護這家車店。前一天夜晚,離這家車店不遠的另一處停車場被縱火。多米尼克和凱爾都不是“克諾沙衛兵”的成員,對這個組織一無所知。他們問前來響應號召的人,但誰也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底細。
夜幕降臨,多米尼克爬到房頂,持槍俯視街道,不遠處警察的裝甲車正驅散示威人群。凱爾在地面一層,混亂中消失在多米尼克的視線之外。街上響起槍聲,多米尼克以為是警察在放催淚彈。旋即,他的電話鈴響了,傳來凱爾驚慌的聲音:“我沖人開槍了。我沖人開槍了。”凱爾再度出現在多米尼克的視線中時,舉著雙手走向警察的裝甲車,一名女警官抬手示意讓他離遠點。凱爾跑回維修店,對多米尼克說:“如果我不開槍,可能已經死了。”多米尼克意識到兩人都闖了大禍,告訴凱爾把槍放到他汽車後背箱,趕快離開。在開車去安提阿的路上,多米尼克告訴凱爾:“我想我的麻煩比你的還大,你是自衛。但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該有那把槍。那把槍在我名下。”
凱爾到家後,告訴母親殺人的事。他母親說:“你有兩個選擇,或者快點跑,或者去自首。”凱爾說要去自首。第二天,凱爾與多米尼克去警局自首。多米尼克追悔莫及,對審問他的執法人員說:“不知道為什麼,當時一直在想,他還不到18歲。頭腦中也清楚,我可以叫停。但我知道,如果不把槍給他,他會發火。”多米尼克以非法向未成年人提供致命武器導致死亡的指控被起訴。凱爾則以兩項謀殺罪、一項謀殺未遂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被起訴。
經過電視報導和社交媒體傳播,凱爾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位名叫林·伍德(Lin Wood)的喬治亞州律師透過自己掌握的基金會,以為凱爾辯護的名義募捐,以凱爾律師的身份接受媒體採訪。伍德並沒有刑事辯護經驗,也沒有威斯康星或伊利諾伊州的律師執照——他只有喬治亞州的執照。不久,一名洛杉磯的民事訴訟律師約翰·皮爾斯(John Pierce)加入,跟凱爾的母親一起在媒體上募捐。皮爾斯跟伍德一樣,沒有刑事辯護經驗。他本人和以前的事務所在加州是幾起民事訴訟的被告,被控欠債不還。凱爾被引渡到威斯康星法院受審,法庭駁回他律師的自衛申辯,將之作為謀殺案和謀殺未遂案審判。法庭允許凱爾以200萬美元保釋。林·伍德和皮爾斯用募集的捐款支付了保釋金。
2020年11月大選過後,民眾對克諾沙事件的興趣不再,關注的焦點轉移到大選結果爭議上。林·伍德的基金會以凱爾的名義募集了數百萬美元后,轉而以為特朗普訴訟的名義募捐。伍德在媒體上宣佈,基金會的主要任務已經轉移到推翻總統選舉結果。他請公眾以後直接向皮爾斯捐款。
威斯康星檢察官請求法庭責令皮爾斯將募集的捐款作為律師費存入信託賬戶,以防被挪用,指出律師債務纏身,可能會把應該用在被告身上的捐款拿去還債。把客戶預支的律師費存入信託賬戶,這是各州律師行業的基本要求。伍德和皮爾斯以非營利基金方式募集的捐款缺少嚴格監管。如果皮爾斯想在威斯康星做被告的辯護律師,必須把捐款作為預支的律師費,按照行業規範存到客戶的信託賬戶中。皮爾斯不願遵守規定,退出了刑事案代理,但仍然稱自己是凱爾母子的民事律師。
2021年2月,凱爾母子告知媒體,已經中止跟皮爾斯的客戶-律師關係,並指責皮爾斯挪用以他們母子名義募集的捐款。
《憲法》第二修正案
在美國,槍不只是一件武器,而且是一些民眾自我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標誌性符號,也是美國特有的草根正義的象徵。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這樣對比歐洲的官府正義和美國的草根正義:“在歐洲,罪犯在逃時被官員擒獲,算他自己倒黴,居民在這場鬥爭中只是旁觀者;但在美國,罪犯都被視為人類公敵,人們群起而攻之。”當時是19世紀30年代。近兩百年間,托克維爾觀察到的一些現象已經消失,很多傳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些傳統依然如故,只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克諾沙事件之後,一些民眾把凱爾作為維護第二修正案擁槍權的英雄,另一些民眾則把他作為非法持有武器行兇的歹徒。
美國槍擊事件頻發,透過媒體報道和社交媒體傳播,經常在社會輿論中引發軒然大波。擁槍支持者和反對者各執一端。反對者要求政府嚴格控制槍械,以減少槍擊事件。支持者則擔心,嚴格控槍之後,不法分子依然有渠道獲得槍支,而普通民眾將失去自衛工具。政黨和政治人物自然不會錯過利用這個話題爭取選民的機會。每次總統大選,《憲法》第二修正案都會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
從字面上看,第二修正案保障各州建立民兵的權利和人民擁有武器的權利。但它是隻保護民兵的持槍權,還是也保護個人持槍權呢?對此,第二修正案語焉不詳。2008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Washington D.C v. Heller)案的判決中首次對這一問題做出澄清。第二修正案原文是:“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現有的中文翻譯將第二修正案譯成“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所以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按照“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的判決,中文翻譯儘管只加了一個“所以”,卻不符合第二修正案的原義。
最高法院認為,“一隻管理良好的民兵”只是第二修正案的開場白,講擁槍的目的,但在語義上並不限定“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這一核心內容。“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第一次確認,持槍權是公民的個人權利,不是民兵的集體權利,不需要與民兵有關。從法理上講,持槍權源於人自我保護的自然權利,先於《憲法》。從法律史的角度講,“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實際上是把普通法的自衛權變成了一種憲法權利。按照這一判決,第二修正案講的“人民的權利”必然是個人的權利,而自衛針對的物件可以是政府的暴政、外敵,也可以是個人。
在此,有必要對“權利”做粗略的辨析。現代漢語學習西方語言,講“權利”至少有以下幾層語義:第一是作為政治理論或法理前設的“自然權利”,在西方傳統中源於自然理性或天啟;第二是宣言和公約中作為政治宣示的“政治權利”,屬於政治理性或政治想象的範疇;第三是法律法規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定權利”,屬於法律技術,或用愛德華·科克(Edward Coke)的術語講,屬於“人工理性”的範疇。 “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事實上創造了一項新的憲法權利,即個人自衛權,或個人擁槍權。
在經驗層面上講,槍支客觀上消弭了個體之間體力的差距,使得原本體力處於弱勢的人在面對罪犯時也有力量自衛。在美國法律中,自衛的目的是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身體免於受到傷害,在無可規避的情況下,可以採取一切手段,包括致命手段,而無需考慮兇手罪至幾何——那是法院的工作,不是普通民眾在生命和身體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所要思考的事情。
“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的判決不只是個憲法理論問題,也體現了美國特有的歷史傳統。在治安制度方面,美國早期承襲英國的治安官(Sheriff)制度,由民選的治安官進行執法。但是由於地廣人稀,稅收有限,治安官數量少,通常難以及時趕到案發地執法。因此,民眾不得不自行執法,將擒獲的嫌犯交給治安官收監。直到如今,很多州依然是治安官負責管理監獄。各縣從治安官到檢察官和法官均由民選產生,而且由民眾組成的大陪審團最終決定是否起訴犯罪嫌疑人。所以,治安官傳統與後來出現的警察機構不同:前者由人民直選,對人民負責;後者,由政府任命,對政府負責。
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當今美國社會對民間執法的草根正義仍然有較高的容忍度。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傳統仍然會延續下去。問題在於,民間執法的法律邊界並不清晰。而且,克諾沙槍殺案不同於“華盛頓特區訴海勒案”:凱爾不但非法持有槍支,而且主動帶槍進入衝突的環境。不過,從現場的影片看,凱爾在開槍時被人追打,一位被他擊中受傷的人手裡還有槍。證據並不完全對檢方有利。
審判
2021年11月1日,克諾沙縣巡迴法院開庭,由布魯斯·施羅德法官(Bruce Schroeder)審理凱爾·裡滕豪斯案。在挑選陪審團的過程中,第二修正案又成了焦點問題。一位候選人說,因為他平時積極支援第二修正案,不相信自己能在本案中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斷,所以請求退出。施羅德法官對他說:“我不在乎你對第二修正案是什麼意見……我想讓這個案子反映出克諾沙的偉大,克諾沙的公正,不想讓這個案子偏離到別的問題上去。”他指示陪審團排除政治和媒體的干擾,只看法庭上的證據:“這個案件已經很政治化。你們能讀到各種政治光譜的案情評論,大多數是些什麼也不知道的人寫的。”
從挑選陪審團開始,一些專家和學者就批評施羅德法官偏袒被告。在審判過程中,這種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多,尤其是當他跟檢察官當庭發生言語衝突之後。檢察官試圖出示已經被施羅德法官否決的證據,遭到當庭斥責。幾位關鍵證人的證詞對檢方不利。一位當時在現場的攝影記者作證說,他看到第一位被凱爾開槍打死的人追打凱爾。一位被凱爾擊中後倖存下來的證人承認,他當時拿著槍追趕凱爾。凱爾自己作證,被他的律師和檢察官質詢了幾個小時,反覆講他害怕槍被奪走,害怕被追趕他的人打死。大部分時候,他表現得比較平靜,但說到一些細節,開始哭泣。他母親坐在旁聽席上不斷擦眼淚。
審判持續了兩個星期。11月15日,庭審結束,陪審團經過三天審議,判定檢方對被告的所有六項指控不成立,法庭宣判凱爾無罪。審判結束後,各方的爭辯和爭論從法庭轉移到媒體上。法院用法律和證據審判被告,評論家用自己贊成的理念審判自己反對的理念,跟風群眾用自己喜歡的口號審判自己不喜歡的口號。每個備受關注的案子發生後都是這樣。但魔鬼在細節中,上帝也在細節中。對一個判決結果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評論家和公眾不感興趣的一些案情細節。
施羅德法官顯然同情凱爾,這可能會影響到陪審團的態度和判斷。但很難說這是導致判決結果的決定因素。檢方指控的三項嚴重罪行沒有被定罪,看了關鍵證人的證詞和證據後,不覺得意外;但三項輕一些的指控沒有被定罪,法官和陪審團的同情心顯然起了很大作用。可能在陪審團的眼中,凱爾是一個出身不幸家庭的少年,從小喜歡當警察,在成年人的衝突中,把自己想象成警察的幫手,要帶槍去保護私有財產。很多男孩子會有這種幫助正義力量執法的想像,只是很多男孩子比凱爾幸運,有負責任的父母,家裡有像樣的收入,能唸完高中。這可能是凱爾跟很多男孩子命運最不一樣的地方吧。
對於這個審判結果,老實講,筆者不知道是對還是錯。在對錯晦暗的混沌中,最強烈的感覺是悲哀。想到作家威廉·福克納的一段話:“如果我們美國人已經在我們的絕望文化中到了謀殺孩子的地步,不管是什麼原因,不管是什麼膚色,我們不配生存下去,可能也生存不下去。”當時,幾位密西西比成年人殺了個黑人少年,據說原因是他衝一位白人婦女吹口哨,陪審團說他們無罪。福克納的激憤之語,反過來說道理一樣:一些成年人以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名義把一個帶槍的孩子忽悠到街上,以殺人告終,不管什麼原因,這些成年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在面對面的街頭衝突中,成年人尚且難以完全理性地處理複雜的情況,何況一個十七歲的少年?除了發生悲劇,還能有什麼結果?即便被判無罪了,少年時代經歷了這些,殺了兩個人,職業前景渺茫,人生會變得異常艱難。這是場不負責任的成年人忽悠出來的底層年輕人的悲劇。這個事件中,最應當被審判的是那些把這孩子忽悠到街頭開槍的成年人。但他們在法律的邊界之外。
凱爾·裡滕豪斯案審判結束了,但他姐姐的男朋友多米尼克的案子還沒有了結。正像事發那天晚上,多米尼克對凱爾說的那樣:“我的麻煩比你的還大,你是自衛……但那把槍在我名下。”多米尼克以非法向未成年人提供槍支罪被起訴,8月的時候,他的律師和檢察官同意,等凱爾的案子判決後,再安排開庭時間。媒體對多米尼克的案子沒有多少興趣,年初時有報道說,他向民間募捐僱律師,只收到幾百美元捐款。
最初代理凱爾的兩位律師,約翰·皮爾斯和林·伍德,為爭奪他的保釋金,矛盾早已公開化。9月22日,離開庭不到兩個月,當地報紙《米爾沃基前哨報》報導,皮爾斯要求法庭在審判結束後,把200萬美元的保釋金轉到他控制的帳戶,林·伍德要求把保釋金退還到他控制的帳戶。審判結束了,按照威斯康星法律,法院會在三十天內退還保釋金。凱爾被判無罪的第二天,他的辯護律師馬克·裡查德接受CNN採訪,指責林·伍德在等待審判期間讓凱爾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稱林·伍德“蠢貨”,說皮爾斯和林·伍德心思都用在了“拿這孩子搞錢上”。
林·伍德給馬克·裡查德發電郵,稱他的指控不實,說讓凱爾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都是皮爾斯的主意,跟他沒關係:“你在CCN訪談中公開說我是蠢貨。不對,我不是……在此正式要求你立即收回並更正對我的不實指控。”林·伍德警告馬克·裡查德對,如果對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我會起訴你。”
劉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