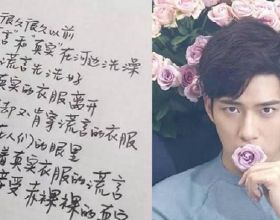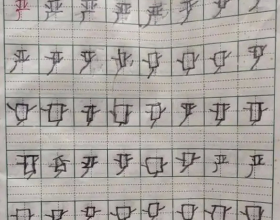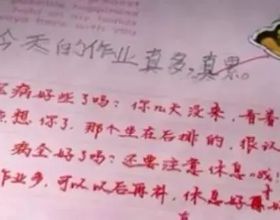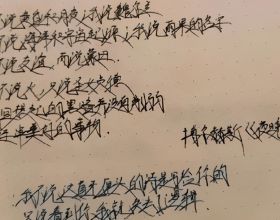2016年的9月11日我寫了篇 《“教匠精神”》,算是關於教師節的文章。又在2018年4月寫了篇《文身與文化,老師和神》,感嘆“老師”和“神”一樣,越來越不值錢了。2020年6月,我寫了篇《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小學生作文,大學生作弊》,悲傷於當今的師生關係。轉眼到了2021年,正宗的“教師”和不正宗的“教師”已經淪落到了可能成為“不法分子”的地步了。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啊!
2015年的6月到8月間,我曾“奮筆疾書”,寫了故道教育漫談的系列文章。從《起跑線》到《迴歸線》,直至最後的《教育漫談終結篇:“重回故道,重識漢字”》(故道教育漫談(2015全集),一直呼籲讓教育迴歸到其本質,不要陷入“惡性迴圈”(因為當時還沒有“內卷”一詞)。
如果你足夠有耐心,看完之前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會發現無論作為老師還是家長,我早就對雙減政策出臺之前的這十幾年的教育亂象表達過不滿,卻又被無奈裹挾。現在是要“天亮”了嗎?
我曾在《起跑線》一文中寫過:“功利性的社會價值觀必然催生出功利性的教育,功利性的教育又繼續培養出更功利的人,中國的教育與社會就這樣進入了一個惡性迴圈的怪圈。”;“有什麼樣的父母未必就一定有什麼樣的孩子,但有什麼樣的社會一定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有什麼樣的教育也一定會形成什麼樣的社會!為什麼這麼多家長自覺不自覺地都不願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什麼報章雜誌、新聞媒體,兒童心理學家、教育專家統統在呼籲這是個偽命題,小時候好未必代表將來好,人生的路還很長等等,而家長們依舊置若罔聞,不惜一切代價逼著孩子學這學那?很多教育從業者歸咎於家長的焦躁心理及攀比情緒,而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拿家長說事是最容易的,逃避責任也最輕鬆。”
所以當我看到相關部門鼓勵學生家長“舉報”補課老師,執法者破門而入;家長付錢補課,成績提高或考試完畢後反手一個舉報(堪比“二奶反腐”)等等新聞之後,頗為恍惚:這是要讓本該相親相愛的老師和家長變成相害相殺嗎?陷入焦慮的家長花錢找了認為可以解決問題的老師和培訓機構,其根本原因是出在教師和培訓機構上?這焦慮是培訓機構忽悠出來的?我完全相信有一部分是被他們有意擴大了,但家長對孩子的未來以及自己未來的迷惘和焦慮又豈是老師和培訓機構有能力造成的?當然,製造底層矛盾同樣很容易,甩起鍋來照樣也很輕鬆。
寫了這麼多,當然不是為那些課上不教,課外收錢猛教的老師鳴冤叫屈。對那些從事於學科類加碼培訓的非編制老師及培訓機構最多是表示同情。但畢竟也曾一時風光無限,有些人也已賺得盆滿缽滿。雙減政策一來,這些機構和老師改弦更張也完全來得及。只是不曾想卻是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掛著“素質培養課”的羊頭,繼續賣“學科培訓課”的狗肉,這讓我們這些以培養孩子們文化素養和獨立思考能力為宗旨的老師情何以堪?
有訊息說,針對上述“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教育局又要開始嚴查了,我倒是樂見其事,唯獨擔心矯枉過正,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一起倒了。聽說鑑別課程是“羊肉”或是“狗肉”還有“專家鑑定”,我倒是很樂意有專家來聽我的課,因為我的課向來歡迎家長坐在孩子們後面一起聽的。但又聽說即便經過“專家鑑定”也未必能作數,最終拍板的還是相關掌權者,這是否意味著有可能“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呢?
對於研究文字的我來說,玩文字遊戲豈非駕輕就熟?反正現在阿狗阿貓都可以叫“老師”,我就做個老師好了,比起“教師”這種已然成為“高危”的職業,至少既能“苟且”又可追求“詩和遠方”。但我卻一直在思考一連串問題:雙減政策既然減輕了孩子們在課業上的負擔,能否在品德方面加強教育呢?我們能否讓一個人的學識和品德成正比呢?但品德這件事又如何來衡量呢?用分數嗎?做好事的數量嗎?當一切被分數化,是否又會出現一大批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其品德之所以“高尚”,是因為分數的需要,而不是自我的“需要”。這樣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偽君子”,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更可怕?
唉,我怎麼又開始“憂國憂民”了呢?我更應該擔心自己“尚能飯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