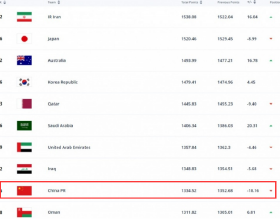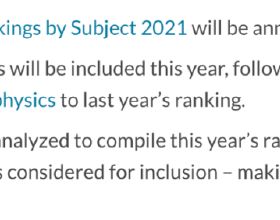上班時間逼近,
我的心情就像被主人打怕了的狗
如果你在網購後緊盯物流狀態,就會發現物流資訊有時會在夜間更新,顯示“您的訂單經某地中轉重新發出”——實際上,這是包裹來到了物流中轉場被重新分揀的緣故。
本文的作者阿穗就曾在全國最大的物流樞紐中心工作過,每天經由這裡的包裹有數十萬件,當人們熟睡時,上夜班的分揀工們卸貨、分揀、打包、裝車,維持著物流鏈條低廉而高速的運轉。
以下是阿穗在中轉場的經歷。
一
在晚上醒來的分揀場
2017年5月,我身上的錢已所剩無幾,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我來到廣東順德的國通物流園,進了德邦的分揀中轉場上班。
我應聘的是理貨員,這是一個需要長期上夜班的崗位,從晚上7點工作到次日早上7點,每個月休息4天。
除了德邦,物流園內還有京東、唯品會、百世快遞等物流公司。郭嘉亮攝
物流理貨是個體力活,面試基本是走個形式。你可以不懂寫字,但要能認字,否則就沒法讀出標籤上的目的地。有時還要簽名,當然也可以找人代簽。
入職前的3天試工是無薪的,這是物流業的行規。試工後,留下的人一半都不到,有的甚至試了2小時就走了。很多人從老家出來,身上的盤纏不多,考慮到這點,公司規定幹滿20天后就能提前拿到頭半個月的工資。
物流園附近的一面招工牆。作者供圖
早上10點,面試結束,人事把我們帶到偌大的分揀場,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揀組,晚上就來這裡報到。
原本以為,工作12個小時不可能每一秒都在忙,試工的第一晚,我還揣了個Kindle,想著閒下來時可以讀些書。但萬萬沒料到,那天晚上我從開始幹到結束,連開啟Kindle的機會都沒有。
在分揀場等待開工的夜班工人。郭嘉亮攝
晚上的分揀場和白天是兩個樣,白天時場內闃寂無人,晚上則一片燈火通明,到處人影憧憧。登上工作臺後,一陣延綿而沉悶的轟隆聲從遠處傳來,原來是幾十上百輛電叉車同時碾軋地面時發出的聲音。
還不到晚上7點,早到的人有的在玩手機,有的趴在工作臺上休息,沒人來和我介紹一下情況。他們似乎都不大喜歡說話,我於是自顧自四處打量。
整個分揀場就像一個大埠頭,貨車在地面穿梭,工人在1米高的工作臺上幹活。工作臺約莫有8到10個足球場那麼大,四周是一個個編了號的裝卸貨口,一排排貨車屁股朝著工作臺停靠,開啟後廂門裝卸貨物。
這些是營業門市白天攬收的快件。我們的工作,就是把這些快件按照目的地重新分揀,然後用纖維袋分別打包運走。
分揀場全景。作者供圖
很快就開工了,組長讓我負責分揀環節的第一步——“倒包”。
從門市營業點送來的快件是用纖維袋打包好的,“倒包”就是把袋子割開,把快件倒出來。一旁的補碼員會用紅外槍掃描快遞單上的條碼,再按目的地補上手寫編碼,然後把快件扔上傳送帶。他們的動作乾脆利落,馬克筆劃拉得飛快,開始的時候,我盡了最大努力也跟不上。
分揀場有5張分揀臺,左右各站一人,一人負責“倒包”,一人負責“補碼”。作者供圖
當快件透過傳送帶來到下游時,兩邊的揀貨員會按照手寫編碼對快件進行“粗分”,丟到對應的帶輪鐵筐裡,再推去分揀櫃裡“細分”。我們一共有10多個分揀櫃,每個櫃處理不同的城市。
傳送帶旁的分揀員負責把快件 “粗分”。作者供圖
分揀櫃是一個像蜂巢般的六角形櫃組,合共48個櫃格,每個櫃格代表一個目的地城市。
“細分”時,一人站在櫃子中間負責投櫃——先把快件舉到控制儀下的紅外口掃描,這時目的城市對應的櫃格會亮燈,然後把快件扔進去。扔對了感應燈會自動熄滅,扔錯了會有蜂鳴音提示。
分揀櫃約2米多高、3米多寬。圖中紅圈的位置就是掃描器。作者供圖
每個分揀櫃一晚上要處理近萬個快件,這就體現了“補碼”的重要性——讀地址是很費時間的。一個熟練的補碼員1小時最多能補3000多個快件,接近每秒1個;而傳送帶旁的分揀員就像在電動遊戲廳裡玩投籃遊戲,根本沒時間把快件拿起來看,掃一眼,就飛快地把快件扔進不同的鐵筐裡。
假如他們用讀地址的方式工作,效率恐怕要降低一半以上,而且還很容易出錯。
德邦早已經是上市公司,但仍然是透過人手分揀快件。圖為分揀場裡的傳送帶。作者供圖
分揀櫃作為最後一環,承受的壓力也最大,一般是兩人為一組工作,一人在外面打包,一人在裡面投櫃。開往不同城市的貨車,發車的時間各不相同,負責分揀櫃的人要背下這組櫃子48個城市的發車時刻表:比如發珠海的是3點,發東莞3點15,發貴陽3點半,髮長沙3點45……忙起來的時候,人很容易就忘記。
我後來負責分揀櫃時就誤過幾次時間,當時我既困又累,精神恍惚,加上發車時間經常更改,很容易忙中出錯。一旦分揀櫃沒趕在發車前清空相應城市的快件,那麼這些快件就要在中轉場裡多耽擱一天,同時我也會被記一次失誤,影響月末的工資評級。
傳送帶的末端打包口。作者供圖
在所有崗位裡,補碼相對而言是最輕鬆的,儘管對手速有很高的要求,但不用搬重物,一般安排女同事做;最累的是倒包,這也是唯一隻能由男性來做的崗位。
一包快件平均有二三十斤,最重的能有六七十斤,要搬起來倒到1米高的補碼臺上——聽起來好像不難,只幹一兩個小時,相信大多數人都遊刃有餘——但我們要連幹10多個小時,一晚上倒幾百甚至上千個包。
每晚進入工作狀態後,大家都像火燒眉毛,都感覺自己不像人,而像機器:手臂彷彿在自動運作,眼睛則像在速讀識別,久而久之,眼手協調都形成條件反射了。
分揀場外等待發走的貨車。郭嘉亮攝
快件在傳送帶上源源不斷地流過,大部分崗位上的人一刻都不能停,有時連廁所都不能上。快件一旦揀不過來,就會全部流到最下游,在那裡堆出一座小山,這時,上游補碼的人要立刻調到下游來幫忙分揀。
堆積在傳送帶上的快件。作者供圖
當時組裡有個中專剛畢業的妹子,個子瘦小,舉止斯文,組長安排她在傳送帶旁揀貨,她就經常揀不過來。每次她掉鏈子,大家就要幫她擦屁股,所以人人都討厭她,不但背後數落她,給她起難聽的外號,當面也會挖苦她,甚至板起臉不理她。
組長和她是老鄉,就勸她另找一份輕鬆的工作。但她男友也在這裡裝車,她想兩人在一起上夜班,生活可以同步,所以不願意走。
後來有一天,她終於因為壓力太大崩潰了,覺得別人在故意整她,幹著幹著就哭著跑掉了。
組長看見她跑了,終於鬆了一口氣。
二
在這裡,弱者就是原罪
第一天倒包倒到天亮時,我的手臂幾乎都舉不起來了,而且肚子餓得要命。
我們晚上幹到9點,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試工的頭天我不知道,是吃了晚飯才去的,到9點時組長讓我跟著大家去飯堂,我說還不餓,他也沒多提醒。
不曾想大家吃完飯回來,就從9點半一口氣幹到早上7點。有的人帶了麵包餅乾,就抽空往嘴裡塞點;有的人什麼都不吃,習慣了餓肚子;我既沒有帶麵包餅乾,也沒有習慣餓肚子,那晚過得苦不堪言。
幹活時的右手,灰塵附著在出汗的毛孔上,汗乾透後形成了灰色的花紋。作者供圖
剛開始倒包時,我連用刀割開纖維袋都要花半天時間,因為不懂技巧,我反覆拽袋子,把兩隻食指的指甲都拽反了,後來變黑脫落,直到兩三個月後才長出新的來,但當時我都沒感覺到痛。
感謝父母,我的體格還算湊合,對於那些體質不好的人來說,這份工作確實幹不下來,你再有毅力,但舉不動貨物,能怎麼辦?
左手同樣。作者供圖
入職時,見我讀過大專,在工人裡不多見,人事部的小哥還問我為什麼來做這行。
說來話長,我畢業後,做過圖書編輯,女裝生意,也輾轉到過雲南、上海打工。2015年,我和朋友在廣州開網店,慘淡經營2年多,還是失敗了。
於是回到故事開頭,我來了這裡。
德邦制服自拍。作者供圖
我們組有50多人,但我一個人說過的“謝謝”可能比其他所有人加起來都多。因為講禮貌,最初我被人認為是軟弱、吃不了苦的。試工時,一個補碼的女孩就覺得我“文質彬彬”,不像個幹活的人,怕我手腳慢,拖累她的計件量,影響她的工資,要求組長把我換走。
我們每人每月按計件量評為A、B、C三級,稅後工資在當時分別為5100元、4700元、4300元左右,根據每個月的貨量增減會有輕微浮動。但以上只是硬指標,組長會根據每個員工的工作態度和實際表現調整評級,然後提交經理審批。
那個看不起我的女孩,實際上就是因為幾個月沒評上A,心裡憋了氣而已。一旦我幹下來,他們很快就對我改觀了。
在分揀臺,手套上是我的名字。作者供圖
這份工作能幹長久的只有少數,因此公司總是在招人。人事部也盡力了,路口擺攤子,牆上貼招聘,APP發廣告,多管齊下,長招不懈,只要有人來應聘,不問三七二十一,先丟到場裡來試工。於是有些不太適合的人,也被送了過來。
位於石洲村的招工現場。郭嘉亮攝
組長最怕的就是看起來弱不禁風的人,一是怕他幹活慢,拉低整體勞效,二是怕他吃不了苦,幹一兩個月就跑,因此試工的時候會故意為難他們。一般這種人試完都會跑。
我們組裡還有兩個殘疾人,是政府硬性攤派來的。每個企業都要接納一定的殘疾人,據說之前因為沒達標,我們還被扣罰過。所以大家開玩笑說,哪怕不幹活,光請他們回來坐著,都能幫公司省錢。
殘疾人其實能幹活,只是因為身體不便,不能輪崗,比如倒包和打包他們就做不了,因此組長並不喜歡他們。在分揀場裡,弱者就是原罪,因為工作總量和人數是不變的,誰幹活慢意味著其他人要幹更多,在大家都身心交瘁的情況下,沒人會同情弱者。
組長也不容易,每天早來晚走,工資也就比組員多幾百塊,作為管理架構中最小的領導,上有指標壓力,下有違抗摸魚,兩頭都受氣。我們組共3個組長,1正2副,我在的10個月裡就走了倆,流動率比普通組員還高。
招工牆前,看招聘啟事的小哥。郭嘉亮攝
物流行業逢“雙11”、“618”等促銷時期,貨量很大,經常忙不過來。所以物流園裡有多家外包公司,為各家物流企業提供臨時工。
外包工人們今天來德邦,明天去京東,後天去唯品會,每天上的是不同的崗,乾的是不同的活,沒法要求他們熟練。他們也不願意賣力幹活,畢竟幹一天領一天錢,磨洋工磨到7點就完事了——而我們要是當天的活幹不完,就得無償加班。
所以我們對他們既愛又恨——促銷期我們天天加班累到崩潰時,把他們當救星般盼;但私下裡我們常常互相揶揄:你這麼懶,為啥不去幹外包?
午飯時間,一名正式員工在手機app上做有關“安全生產”的線上考試。郭嘉亮攝
有一個入職比我晚幾天的同事,早年當過兵,力氣比我大,但幹活卻比我少,臉皮也比我厚。我一晚上就上一趟廁所,他要上五六趟,其實是去抽菸;我有十分力就出十分,他卻只出六分。大家背地裡都說他服從性差,當初不知怎麼當的兵,可能是被開除的。組長看見他就來氣,經常訓他,他只充耳不聞。
開始時我也對他有氣,但礙於我們同期入職,他對我態度很親切,所以我不好發作。後來我都評上兩次A了,他還一次都沒有,仍舊不緊不慢。可見懶人也有原則,不為金錢所動。
下班時間的物流園。郭嘉亮攝
和社會上很多人比,他每天上12個小時夜班,似乎算不上懶漢。但他既然來了這裡,說明他也沒有不吃苦的條件。他家在農村,母親無業,父親幫人做裝修,手藝一般,掙不到什麼錢。他自己快30的人了,一直乾的都是體力活,也沒有物件。
聊天的時候,他說得頭頭是道,要奮發圖強,改變生活,攢些錢以後做生意,還特喜歡吹牛逼,老說別人幹活不行,尤其愛說組長的管理不行,說假如他當組長,保準讓大家服服帖帖。
但一動起手來,他就又怕苦嫌累、對自己放任自流了。
早上8點半,結束了一晚的工作後,幾名工友在園區外休息。郭嘉亮攝
三
我對黑夜的恐懼,
來自白晝的無眠
平心而論,這份工作很適合我的性格。它不用跟人說話,不用開動腦筋,擼起袖子幹就行了。
廣東一年四季有9個月是夏天,白天太陽把廠房的鐵棚曬得發燙,晚上也涼快不了多少。上班個把小時後,人就汗流浹背了。我買了個3升的水壺裝水,每晚喝光,也不用去廁所,全靠出汗排出。
剛乾這活的人都會掉體重,那個和我同期入職的同事,頭3個月瘦了40多斤,我原本就偏瘦,但也掉了接近20斤。
我在室內晾曬制服。作者供圖
衣服是很難洗乾淨的。因為晚上要搬貨物,難免沾到各種汙漬油漬,人累的時候會想:洗太乾淨沒有必要,第二天還是會髒的。好的洗衣粉洗衣液也不便宜,打打肥皂就行了。
於是衣服晾乾後,還能聞到濃濃的汗味。不過幹這種工作,自然而然就不會介意這種問題了。
德邦飯堂的伙食。下班後我們還要吃早餐,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晚餐。作者供圖
真正磨人的是睡覺,因為日夜顛倒,頭幾個月我一直處在這種狀態:到了凌晨4、5點就困得不行,隨便往哪一靠就能馬上睡著。幹起活來就像行屍走肉,目光是恍惚的,意識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麼。
因為這個緣故,有一次我把兩包貨物的標籤貼反了,把重慶的貼成了北京的,北京的貼成了重慶的,幸好在裝車前就發現,被追了回來。
早上7點,下班的員工點起一根菸提神。郭嘉亮攝
後來我在網上跟人提到這段經歷,有人不解地問:為什麼物流分揀都在晚上工作,白天就不能幹嗎?
這是因為白天是門市營業時間,快遞員攬收的快件,集中運到分揀中心已是深夜。此外快遞員每天派送的快件,也必須在天亮前運到門市。假如分揀中心和營業門市都在白天工作,那麼今天攬收的快件就要明天才能中轉,別說“省內次日達”無法實現——那些中途多次中轉的“省外件”和次級中轉到地級市、縣、鎮的快件,每中轉一次就意味著多延誤一天。
即便分揀場通宵達旦,很多人還覺得“不夠快”。我開網店的時候,每天客服都要接到幾十上百條催件留言,有的甚至以此要挾退貨和給差評。
我租住在城中村,這是每晚上班的必經路。作者供圖
黎明前被睡意折磨得走投無路時,我總賭咒下班後一定要立即狠狠睡上一覺。可是到了早上下班時間,人又變得不困了。
人在從事完重體力勞動後,心裡會渴望做一些放鬆的事情來補償自己。有個別同事經常下班後去唱K,唱到下午睡一兩個小時又來上班。我不想把命丟在工作裡,所以採用一些溫和的方式:早餐吃好一點,去超市買買東西,或者聽聽音樂,調節心情。
圖為物流園附近的羅亨村,我就住在粉紅外牆那棟。作者供圖
我住的屋子夏天有30多度,為了能睡著,我想了很多辦法:聽說黑巧克力有助睡眠,我就把它當藥吃,睡前吃一塊,這當然不管用;我又買了褪黑素,也完全沒有效果。
最後只能喝酒。超市裡有4升裝的二鍋頭,紅星的貴,我就買四川產的雜牌,價格很便宜。
喝酒也要花時間,我一邊喝一邊看書,有時候要喝上二三兩才能躺下。
我租住的單間沒有空調。
為了保證睡眠,我儘量避免網購。
我所住的羅亨村生活並不方便,這裡沒有超市、髮廊、食店,只有兩個小賣部,商品少得可憐。村裡的快遞員都不上門,只在村口打電話叫人出來取,我去取一趟快遞要10多分鐘。白天的睡眠本來就脆弱而易碎,萬一被電話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著了。
在我給自己劃定的消費水平內,我偶爾也會買好一點的酒,比如500ml裝的老村長,18塊錢一瓶,是這個價位裡最好喝的。
我要在傍晚6點半起床,假如中午2點前能睡著的話,我就會感到慶幸。如果過了4點還不能睡著,我就變得更焦慮了。
睡醒後的我還是醉醺醺的,每一腳踏下去,都感覺路面的高度不相同。假如沒有醉意,我就會感到睏乏,覺得就像完全沒有休息過一樣。
路過一排出租平房,聞到屋裡傳出的飯菜香味,看到別人已完成一天的勞動正愜意地癱坐在沙發上,我就覺得這樣真是幸福——我甚至還沒有開始幹活,就已經比他們更累了。這時候我就會惡毒地咒罵自己,我的身體咒罵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罵我的身體。
我發誓明早下班後要立刻睡覺,可是到了明早,週而復始。
物流園內,一個席地而睡的員工。郭嘉亮攝
因為長期熬夜,我的情緒控制力明顯地下降。後來組裡新來了個大姐,我帶著她在分揀櫃工作,她負責打包,我負責投櫃。她顯然是個混子,叫我別太快,儘量少乾點。我不理她,按自己的節奏幹,結果她各種磨蹭,拖拖拉拉。
櫃子的快件已開始堆積了,在停下來幫她打了幾次包後,我終於忍不住對她破口大罵,罵到組長來勸架為止。罵過後她果然老實了,或許在這種情況下,罵人才是高效的溝通方式。
有時我甚至想打人,大概是因為不堪重負而變得歇斯底里吧。反倒是那些經常偷懶的人脾氣都好,大概他們也有點心虛。
“我就是這麼強大,我很愛我的工作”——早上7點,園區播起了歌,下班的員工一邊哼著歌,一邊走出園區。郭嘉亮攝
2018年春節的時候,我們理貨部門建了個微信大群,拉進來400多人,各組組長和經理按照慣例發紅包。
我從來沒進過這麼多人的群,大家都在互相拜年,抬槓,起鬨,發自己老家的照片,轉來轉去的賀年表情,幾秒鐘裡能拉出十幾屏長的聊天記錄,比看春晚熱鬧多了。
我已經很久沒過過這麼溫暖和熱烈的春節,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搶紅包。手機太卡,很多紅包我都錯過了,最後總共只搶了十幾塊錢,我又發回到群裡了——高興是用錢買不到的。
石洲市場內,一起吃老麻抄手的工友們。郭嘉亮攝
因為我服從性強,從不抱怨,春節放假前,經理請客做東,上館子擺了一桌,除了3個組長和1個助理外,只叫了4個普通組員,我是其中之一。吃完這頓飯後,組裡所有人都說,我們將是部門重點培養的物件。
可長期熬夜會增加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實際上,我已經感到腦子不好使了。面如死灰的外表下,我反應日漸遲鈍,記憶力開始衰退。為了延緩大腦的退化,我開始吃堅果。附近的石洲村能買到的花生和瓜子,我幾乎都吃過;核桃能買到一種殼不厚不薄的,往地上用力一摜,它就從中間裂開了。
但核桃並不能預防阿爾茨海默病。2018年的3月,在德邦工作了10個月後,我決定辭職。次月,我進入順豐改做快遞收派員,從此不再上夜班了。
雖然快遞工作也很累,但不用熬夜,身體負擔沒那麼重。作者供圖
眨眼過去兩年,我微信裡還有不少當時的同事,從朋友圈的內容看,他們大多都已離開了。
我的變化也很大,現在的我不再罵人,更不想打人。不過,我還在堅持吃花生、瓜子和核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