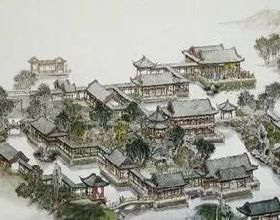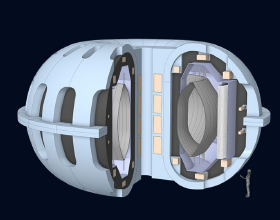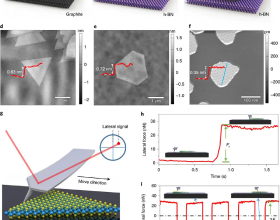更進一步,這種系統的對稱性把歐洲的異質審美注入圓明園。在那裡,18世紀晚期,中國帝王正創造一種歐洲工藝品的同等形式,精確地反映歐洲,反之亦然。乾隆非常喜歡從歐洲蒐集精緻的鐘和機械玩具。紫禁城儲存著數量巨大的蒐集品。1860年在圓明園掠奪的目擊者們描述:房間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鐘和音樂盒子。這些耶穌會士觀察到:乾隆被所有的西方的東西迷住,實際上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容忍耶穌會士是為滿足他持續的娛樂的好奇心(儘管堅定地限制西方的宗教、政治和經濟滲透)。正如阿米特教父所論:“君主在好奇心方面的豐富性和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的壯麗,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在同樣的對差異的娛樂審美的欣賞的基礎上,當乾隆決定模仿歐洲,他做這些在一定的規模上遠遠超過英格蘭和法國的任何東西。郎士寧、蔣友仁和他們同行的耶穌會士在1747年被引導設計一套模仿法國、義大利和奧地利模式的宮殿建築,外部用石質(雖然在木製架子上),搭配精緻的、充滿活力的噴泉(以往在中國的花園裡不為人知),用混合模式的石雕、備置歐洲的鏡子、枝形吊燈、繪畫和壁毯裝飾。
兩座最大的建築是諧奇趣(“令人驚歎的趣味”)海晏堂(“海洋的愉悅之堂”),諧奇趣完工於1753年,且擁有17間房的諧奇趣(“令人驚歎的趣味”),和有完工於1759年且擁有22間房的海晏堂中部有一個巨大的儲水箱。在著名的噴泉水力鍾前,有12個青銅製的獸首,代表十二地支,每個獸首持續性地噴水2小時。這一建築群有好幾座小樓,包括很可能以凡爾賽宮的凱旋門為基礎修建的一個大型噴泉建築群、養雀籠和完工於1783年的迷宮。似乎沒有西方人被允許參觀這些所謂的“西式宮殿”,直到法國和英國軍隊於1860年在這裡遊蕩。他們描述洛可可式的壁毯、模仿安託萬·瓦蒂和弗朗斯哥·布歇的繪畫(他們本人是中國工藝品的實踐者),和來自法國朝廷的美麗的肖像畫。

乾隆認真對待西式建築,並沒有超越歐洲人對待中國建築的態度。王致誠提到:歐洲人對多層房屋的偏愛使皇帝困惑。他引用皇帝的話說:“歐洲必定是一個非常小而悲慘的國家,因為那裡沒有足夠的土地給城市擴張,人們在那裡不得不生活在空中。”西方的宮殿事實上純粹是為娛樂而建造的,它們被當做一個歐洲藝術品的陳列櫃和主題公園。在建築群東部的末端,穿過一個矩形的湖泊,一個裝門面的歐式城鎮街道,以一系列逐漸減弱的戲劇性西方透視法的形式被新增。
這些象徵王權的宮殿坐落在一個小的最遙遠的小角落,從皇帝的寶座所在的殿堂和居所,很可能有些地方是妃嬪的住所。儘管乾隆最寵愛的妃子香妃住在那兒,這似乎僅僅是一個神話,但是香妃在歐洲工藝品方面發揮另一種作用。一位不知名的宮廷藝術家所繪的洛可可式的畫面顯示:她裝扮成一位西方的牧羊女,部分是出於乾隆對喬裝成歐洲人的興趣。正如歐洲人對待中國那樣,乾隆對待歐洲文化,是把它作為一種異域的多樣性,把有意義的象徵歪曲和轉換成一幅具有審美對比的圖畫般的戲劇。
為了完成這個不僅是藝術和建築,而且是一個歐洲可視觀念的整體模式的模擬,乾隆在1783年命令製作一套20個的大型銅板雕刻來代表這些西式宮殿。第一批繪畫完全在中國製作,伊蘭泰(明顯是向耶穌會士學藝術的學生之一)用一種混合的風格繪製這些作品。
這個例證在這裡展示,描繪海晏堂,包括西式的線性透視法,儘管採用典型的中國式的樹葉模式,透過明暗對照樹影的方式放大岩石,但是幾乎沒有投下陰影。在視覺詞彙的混合方面,雖然笨拙但是一絲不苟,印刷品把樓房的多種水平線和不規則曲線翻譯成一出多樣性的戲劇,仿造和對位中國工藝品和歐洲工藝品的典型是同等的。

一個獨特的西方宮殿區域的手工圖畫是這種跨文化對話更進一步的材料來源。是一個獨特的西方宮殿區域的手工圖形。這幅圖長度超過2米,最近在法國國立圖書館的藏品中重新被發現。一位不知名的歐洲收藏者用墨書寫的石碑顯示:這幅圖伴隨著一套“我1787年10月從布林熱瓦先生率領的法國使團在北京的居住地獲得的”20幅雕刻。在這套圖版中,在每一座建築物上的雙語標籤給這種結構以名稱和它的編號。
儘管直接在表面用墨書寫法文(在石碑上用不同的手段),中文標籤是在紙片上用筆和墨書寫的高質量的中國書法,並被貼上在表面。表面本身由2大張中式的紙張組成,附加一個編織的絲綢或背面的帆布。所有這些都被提升為一種中國傳統的立體懸掛式卷軸。但是在一個古典主義西式模式中,有底部鍍金的木頭卷和頂部鍍金的雕刻。作為一種繪製雕刻地圖和重構它們的實際空間關係的方式,整個卷軸在西方幻想主義記錄中(儘管收藏者實際上有沒有見過建築物)似乎是一種練習。但是,它的雙重文化形式和雙語文字使它更加複雜,代表西方宮殿建築群和整個遺蹟所具體表達的跨文化對話精神的混合。

源於這些對稱性的反響和跨文化混融的諷刺,1767年展示給乾隆的博韋【譯者注:博韋是法國北部一座城鎮,位於巴黎西北偏北,花毯作坊建於17世紀。】(不是格貝林【譯者注:格貝林位於巴黎13區。】)的掛毯的命運是典型。在17世紀90年代到1731年之間,法國博韋製造業編織了許多套掛毯,10幅掛毯描繪中國皇帝和宮廷的景象。現實與幻想結合,中國、印度和歐洲元素混合,這些掛毯影響法國整個中國工藝品的詞彙。
在1742年,博韋創造出另一套6幅中國掛毯,這次在精神層面顯得更加洛可可式,想象田園式的而不是朝廷式的臣民:飯、定期集市、舞蹈、漁業、狩獵和廁所。這套掛毯的底圖以大布歇(為蓬巴杜夫人設計中國式閨房和其它中國工藝品的設計者)所繪的彩色素描為基礎。布歇部分是基於王致誠從圓明園帶回的圖畫。
1763年,國王把一套這樣的掛毯賜予赫瑞•貝爾坦,他是掌管法國印度公司的外交大臣。他從耶穌會士手裡蒐集瞭如此多的中國作品。貝爾坦把這套掛毯又賜予了兩名中國人,他們把這些掛毯又帶回給在北京的耶穌會士使團。1767年,這一使團依次代表法國政府向乾隆皇帝展覽這套掛毯。乾隆又一次高興地接收它們,把它們作為西方奇異品的例子。他為耶穌會士使團特別建造了一所房子——瞭望臺來安置他們,就在他的西式宮殿群中。阿米神父1789年描述這座建築物用鏡子裝飾,填滿了昂貴的、一個人幾乎不可能移走的歐洲機器。因此,博韋的掛毯直到1860年法國和英國軍隊在圓明園掠奪時,在聲望和同時期的利潤方面都保持著它的地位。軍人們拿走許多鍾和音樂娃娃,把大堆舊式掛毯視為從一支糟透了的軍隊手中進一步掠奪的物件。英國軍隊在西式宮殿群前掠奪,拿著火把,沿著圓明園剩餘的東西行動。

1860年,英法軍隊對西式物品與中式物品一樣,放肆地毀壞。這暗示軍人們把它們都視為簡單的皇室衰落的符號,即便對自己本國生產的東西也是如此。儘管如此,一名目擊者把這一共享的、超越野心、認同的歐式宮殿和掛毯視為過去的時代共享的皇室文化符號。
一位叫安東尼•福希瑞的隨軍法國記者寫下關於圓明園的最富有敵意的譴責,還曾經出版過。關於這一建築群的特點,他也稱之為“中國的凡爾賽宮或聖克盧”,作為審美上的怪異圖樣和政治上的腐朽。對於他來講,西式的宮殿僅僅是一個可贖的部分,因為它們清晰地顯現熟悉的、與法國文化的聯絡。這些混合型建築物是令人鄙夷的。他寫道:“但是,這種存在於中國人中的細緻精神和對小東西的天生的鑑賞力之間的親密聯絡,這種對小型詩歌、侯爵夫人們、晚餐的喜愛、珍貴、追求,簡而言之,這些瑣碎事物的不幸的疾病,是里舍利約和弗羅薩短暫時代的特徵的一個方面。這些足以給這一模仿的作品(雖然不是完美的)一個相對的價值,那不是沒有優點。”他把中國的審美觀視為是對早期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代幻想藝術的一種反映。
顯而易見的,這種對法國藝術的模仿證明:正如他所斷定的,法國本身必定像中國一樣。“在所有這些(中式的)宮殿中,有一個從尊崇的形式來講是突出的。它是路易十五的宮殿,一座洛可可式的宮殿!特瑞羅、呂西安娜、馬裡,你能選擇!當我們自己在我們的習慣、藝術、倫理和政治中,傾向於如此接近地像中國人的時候,證明:世界上最古怪的人民付給法國如此巨大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心不可能在一個特定的時代之外體面地產生。”這是兩種宮殿文化的相互反映。換言之,這種相互反映只能發生在兩類非常不同的人群享有相似的基礎文化和價值觀。
儘管這種相似性把圓明園和凡爾賽宮放在一個同等的地位,但是似乎到了1860年,凡爾賽宮本身貶值了,作為一個法蘭西自身腐朽的過去時代的遺留物。這一過去時代將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末端,隨著1870年君主制的崩潰。中國和歐洲工藝品在這一時刻互相反映,作為一個可視的、苦樂參半的、懷舊的、前近代皇室秩序的製造者。這在19世紀晚期近代經濟、政治和文化壓力的面前煙消雲散。歐洲工藝品和中國工藝品一樣,已經成為一種貴族衰落的符號。

不同於後來發生在圓明園的東方主義的跨文化交流,因為它們建立在一種法國和中國之間互相平等的認可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互相之間的優越感或自卑感。正如本文的第一部分所顯示,這兩個國家的宮殿文化,以相似的方式實踐,伴隨著相似的生產和傳播系統。
這種基礎性的系統的對稱性,足夠使雙方的參與者們認同兩種宮殿藝術系統的互相反映,儘管在風格和意識形態的內容方面有明顯的和高度可視的差異或歪曲。因此,對中法雙方來講,在雙方的互相反映和歪曲中,形成了發生在圓明園的特定的藝術交流。中國工藝品、圓明園的花園和建築起了關鍵作用,這是一個雙重的過程,儘管強調互相平等的政治/文化體系,但把異域形式上的差異最大化。這完美地從反面反映了歐洲工藝品的過程,儘管包含一個可比性的基礎政治/文化體制,但中國朝廷異域的歐洲形式傳播給圓明園。
在雙方的互動過程中,一方為了文化適應,歪曲另一方的意識形態,抽空它們的土著文化涵義的異域形式,為了改變他者的審美,把他者的父系象徵符號女性主義化。但是,它們如此完美地互相反映,伴隨著再次互相強調君主在本國統治和宮殿文化方面促使它產生的效果。這是18世紀一個特殊的情況,在19世紀更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者手裡,它將不再倖存。
[原著]
格瑞﹒托馬斯
[翻譯]
尤 李
[編輯]
付 懷 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