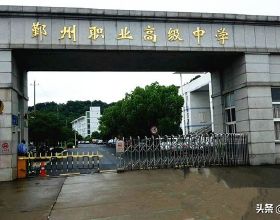看看時間,凌晨三點。嫂子這個時候打電話過來。我瞬間清醒,一下子坐起來。
“…呼…嗚…”零零碎碎的鼻音,間雜斷斷續續的哽咽聲。我的心緩緩沉下去,冷汗順著我的額頭流下來。不說話,因為不敢說話。
“辰辰他,打電話給我了。說了軍訓的事。”呼!心一下子落下去,僵硬的身體軟下來,有打人的衝動。還能不能好好說話了?半夜三更的,會嚇死人的,沒腦子。
不過想想這是六年來兒子給她打的第一個電話,也就釋然了。
我披上一件薄外套,走到窗前,推開窗戶。窗外霓虹燈閃爍,在夜色中很是璀璨。
睡前和侄子的對話重現眼前:“給你媽媽打個電話吧!”我平淡地說。
對面很久沒有聲音,就在我以為不會再有回答的時候:“給我一個理由。”
還是在痛嗎?就像我一樣。我輕嘆一聲:“或許,因為她新長出的白頭髮。”
對面又是一陣沉默,傷痕在撕裂吧。好久以後:“就像你對你媽媽,我奶奶一樣嗎?因為奶奶花白的頭髮,你打了第一個電話。”
“是吧!”我看著窗外。
這一瞬間,我們都清楚地讀到了對方的情緒。愛與恨,渴望與推拒交錯的情緒,啃噬著我們。這是我們都曾被放逐過吧!不管是什麼原因,被放逐了,就是被放逐了。傷了就是傷了!一個好的理由會讓理智原諒,可是心裡的傷要時間來痊癒。也許時間要很長。
他還是打電話了。或許,這是在試著接受了吧。不管是不是,至少已經在開始。
幾個月前,沒有人看好他能考上大學,還是重點政法大學。以他當時的成績,專科線都難。一個學渣。
哥哥嫂嫂,爸爸媽媽,人人心裡著急,面上卻不顯。小心翼翼和他說話,害怕觸怒他。這個孩子,基本不與家人溝通。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
為了他,全家搬回了老家的城市。想要彌補,想要還給他曾失去六年的家。可星期天學校放假也不見他回來。是不是失去太久,太陌生,不想回來了!
小時候的侄子是一個話多的孩子。很漂亮,幼兒園園長看到他,都會忍不住停下來踢踢他的小屁股,輕輕掐掐他的小臉。實在是太嫩了,手感不是一般的好。水靈靈的大眼睛,清清亮亮的歪著頭看著你,心都化了。
他的轉變,是在上完小學。因為超生,不能在父母生活的城市上公立初中。而民辦初中,那真是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為了他的前途,考上好的大學。帶著他急急忙忙地回老家城市,去各種入學考試。最後如願進了一所重點中學。
寄養在二堂伯家。暴躁的二堂伯喝醉酒打他,二伯母不給他飯吃,說他沒有煮飯拖地洗衣服。又輾轉到大堂姑家,大堂姑對他挺照顧,可獨生女兒嫌棄他放學回來太晚吵到她。沒辦法轉移陣地到老姑婆家,才勉強消停下來。
而侄子就在這匆匆忙忙的,連軸轉的各種嫌棄,各種推拒中,變得越來越沉默。這一點並沒有引起遠方父母的注意。待到察覺時,悔之晚矣。
他們都說侄子到了叛逆期,又被家人送到陌生的城市。所以變得很壞,很尖銳,很暴躁,拒絕溝通。只是後來從各處知情人的話語間,聽出了不少不堪回首的寄人籬下。
第一次給侄子打電話是在三個月前。看著哥哥滿眼的無奈,嫂嫂滿眼的無助痛苦。我默然。
他們並沒有太多的孩子,就一兒一女。這是唯一的男孩。他們都知道了吧!自己兒子過得,那是怎樣不堪回首的六年。可你能去責怪誰呢?畢竟那不是寄養家的孩子。別人沒有義務像親生孩子一樣對待。
做父母的肉眼可見的自責痛苦。但對一扇把你關在門外的心扉,你能怎樣呢?
嫂嫂說:只求他願意說話,願意溝通。愛也罷,恨也罷,說出來。父母錯了的地方,通通改。面對痛淚滿臉的嫂嫂,我無聲一嘆。
那天撥了電話過去,對方是默然。
我淡淡的平鋪直敘的對著沉默:“你的成績是故意考差的吧,換了我也會那樣幹。但高考那幾天,如果是我,會好好考。這些年讓我明白,靠山山倒,靠父母父母會老,最後要靠的是自己。還有,你知道的,我比你慘。”
對方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為他睡著了。然後對面有了聲音:“知道了!”
那以後,我們就會通話,簡短几句,就明白對方的意思。我不小心翼翼求著他說話,他也不小心翼翼看著我的臉色慾言又止。被人理解共同分擔很舒服。雖然是姑侄,更像是難友。我們都有被寄養的經歷麼。
我並沒有告訴父母哥嫂侄子的事,這就像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冷眼看父母哥嫂各種焦急卻又無可奈何,滿面愁緒。心裡居然有幾分惡作劇的歡喜。也許,我也還在意難平吧。
意料之中的超一本高分。侄子電話中只平淡地說了一句:“想上政法大學。”
我隨意地回了一句:“好!”
掛掉嫂子的電話,想到她的哽咽和白頭髮。我開啟手機,轉發幾張侄子軍訓的相片給她。相片中,原本的小小稚童倏忽長大,已是颯爽英姿美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