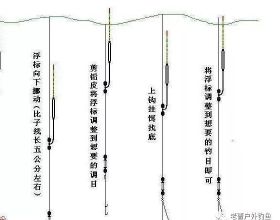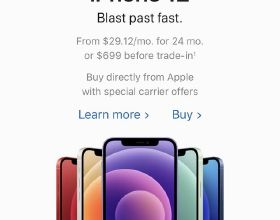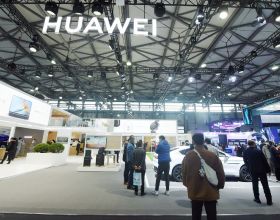必須承認,哈雷不僅僅是一部摩托車。它容納了一切讓男人腎上腺素狂飆的元素——自由、流浪、包容、狂野、財富虛榮、民族主義……
飛行員造就摩托文化
1903年,第一輛哈雷·戴維森摩托車誕生。根據官司言記載,它產自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的一個工棚,由威廉 哈雷和亞瑟·戴維森用雜七雜八的零件拼湊而成。
當這兩個毛頭小夥在工棚裡揮汗如雨的時候,也許偶爾會做過百萬富翁的白日夢,但肯定還沒有瘋狂到把哈雷和所謂的美國精神綁在一起。
直至二戰,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人的二戰英雄除了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和巴頓,還有一群定格在電影裡的飛行員,同時他們也是一幫開著摩托車四處轟鳴的亡命徒,路的一端是空中決鬥、死亡和勳章。
美國飛行員奠定了摩托車文化的全部基礎。除了震耳欲聾的馬達,哈雷騎士最重要的行頭是黑色皮夾克,那是飛行員的專利。影響之深,還可以從戰後蓬勃興起的摩托車俱樂部中看出。其中的典型,就是“地獄天使”。
奧爾森後來回憶,“地獄天使”這個詞,給他的MC(英文“摩托車俱樂部”的縮寫)極大的啟示,最後不僅繼承了名字,還把白底紅字的飛虎隊“地獄天使”的標誌也抄襲為自己的會標,且一定要縫在黑色皮夾克背後。
隨著MC的興起,一出極具美國特色的場景長盛不衰:夕陽下,引擎嘶吼聲中,濃煙滾滾,夾雜著一股燒輪胎的焦味,一群精壯漢子身著一水兒的黑皮夾克,從地平線上飛速駛來,表情木然又透著幾絲得意,胯下是清一色的哈雷摩托車。領頭那個猛男,名叫馬龍·白蘭度。這是20世紀50年代電影《飛車黨》的經典鏡頭。
《飛車黨》取材於1947年的事實事件,史稱“霍列斯特騷亂”。在加州一處小鎮的國慶活動中,美國摩托車協會贊助舉行年度的“吉卜賽巡遊節”,結果從全國擁來4000名摩托車手,場面失控成了打砸搶,最後演變為騷亂。
事後,主辦方摩托車協會聲稱“99%的車手都是守法的好公民,只有剩下那1%的是暴徒。”此語一出,直接後果是在英文中增添了一個詞語——“百分之一的人”,專指反社會的摩托車手和摩托車俱樂部。說來也奇怪,“飛車黨”的模仿物件是飛行員,其群體中也有大量復員軍人。戰鬥英雄們剛剛以生命捍衛的這個國家,怎麼突然就成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物件了呢?
只能說,戰爭越殘酷越刺激,和平就越無聊越沒勁。心態上的落差讓英雄們無法融入正常生活,於是滑入底層。正如某一位“飛車黨徒”說的:“我們就是喜歡炫耀,所以弄出一大堆噪音,然後每個人都會看我們。”
聖騎永遠“在路上”
復員軍人造反,只是戰後美國大變革的胎動。等十幾年後嬰兒潮一代登上歷史舞臺,那對現在秩序的挑戰才叫兇狠。所有的美國價值觀,都在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嚴懲的動搖,或者乾脆重塑,而哈雷摩托,真正地成了“在路上”的流浪者們的聖騎。
這一代哈雷騎士的偶像,顯然出自1969年的影片《逍遙騎士》。長髮、長鬚、長鬢角,身著花襯衫和黑皮夾克的男主角彼得,與朋友開著威風凜凜的哈雷摩托車穿越美國。哈雷出場時,比彼得本人更隆重——通體鍍鉻的車身銀光閃閃,極具視覺衝擊力,再仔細看,那車已經被改裝得像彼得本人一樣瘦長。整部影片裡,彼得都拉著一張冷酷麻木的長臉,開上哈雷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把手錶扔了——標誌著和一切社會習俗決裂。
直到這個鏡頭,“自由”這塊閃閃發光的招牌終於釘上了哈雷文化,此前只有青春期的不負責任和放浪形骸。
騎上哈雷,彼得們飛馳在沉睡的美國南方,尋找自由。他們看到了神秘宗教公社裡一群絕望的精神病人,他們看到了釀酒成性卻又有特權的律師(象徵主流人群)。整個美國已經墮落得不可救藥,於是彼得們帶著妓女去教學嗑藥、亂交。
電影裡有一句著名的臺詞,彼得冷漠地說:“我從來沒想變成別人。”
這句話在社會層面上的效果極其荒謬——“逍遙騎士”不想做別人,可別想要變成他。一時間,按電影裡的樣式改裝的哈雷摩托竟蔚然成風。
可怕之處就在於此——“追尋自由”,但這一行為不再是自由的,而是模仿。嬉皮士的叛逆,在外觀上驚人相似:長鬚長髮不剪,墨鏡不摘,黑皮夾克不脫;在精神上,嬉皮士們紛紛求助於東方宗教和毒品;在目的上,追尋到的所謂“自由”,不過是一種複製的心理感受。集大成之體現,是20世紀70年代名作《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中的一段話:
“它(哈雷摩托)沒有什麼車窗玻璃在面前阻擋你的視野,腳下飛馳而過的是實實在在的水泥公路,和你走過的土地沒有兩樣。它結結實實地躺在那兒,雖然因為速快而顯得模糊,但是你可以隨時停車,讓那份踏實深深印在你的腦海裡。”
哈雷進入了“更年期”
時至今日,隨著汽車工業大發展和更多娛樂方式的勃興,哈雷似乎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更年期”,不過,死忠的FANS至少還對兩件事記憶深刻:其一,是1983年哈雷成立了品牌社群性質的車友會HOG(Harley Own-ers Group)。其二,是1987年5月老兵節,華盛頓第一次出現了“滾雷行動”大遊行。
這兩個方向,使哈雷在商業拓展和文化渲染上並行不悖。HOG現在已經發展到115個國家,80多萬會員,而大遊行發展至今,規模越搞越大,尤其在“9 11”之後,它逐漸演變成了愛國主義大閱兵。
2008年第20屆,共有10萬輛哈雷摩托車大遊行,組成星條旗的海洋。響徹雲霄的引擎聲中,車手們無論男女,一律黑皮衣,牛仔褲,扎著大花頭巾,一臉以身為美國人而自豪的囂張。更不能忽略的是,在反恐戰爭陷入泥淖的當下,歷來華盛頓反戰大遊行的一側,也有擁護布什的反遊行。後者在隊伍裡,插著星條旗的哈雷摩托車也是少不了的組成部分。在全球化和愛國主義的衝突中,哈雷居然毫髮無損左右逢源。因為兩邊都信奉著一個早已似是而非的概念——“自由”,這可是哈雷文化最重要的一道光環。因為信奉自由,所以哈雷騎士在黑皮衣裡穿上一件切 格瓦拉頭像的汗衫,是最恰如其分,也頗為常見的裝束。《紐約時報》上,記者在哈瓦那採訪得知,格瓦拉的幼子居然也是一個哈雷車迷。
但哈雷還是在變老。20世紀80年代,哈雷騎士的平均年齡是25歲,進入21世紀時,成了47歲。現在,頭盔下不再有壓抑不住的長髮和大麻煙味,而是“成功人士”的皺紋和白髮。哈雷騎士不再是飛車黨和嬉皮士,他們考慮的是胯下的哈雷車上該有怎樣的環繞立體聲和衛星定位系統。
2006年,美國《新聞週刊》做了一次網路民意調查:“哈雷摩托的黃金時代是否即將過去?”56%的採訪者選擇了“是的,嬰兒潮一代人頭髮越白,開的里程就越少”。
然而,就此對百年哈雷的走向做悲觀結論,還為時過早。實際上,除了本土的頹勢之外,哈雷文化已經擴充套件到了全球。中國明星李亞鵬就是地道的哈雷迷,他在部落格上毫不掩飾自己對哈雷的興趣:“戴上我的行頭,推出我心愛的哈雷,花了半小時反它擦試乾淨,一絲不苟勝過給自己洗澡。發動點火就像摁Play鍵,低沉而有節奏的轟鳴聲頓時隔絕了這個世界的所有嘈雜。今天是星期天,我的名字是哈雷 李。“同時,在各種哈雷慶典會場,人們開始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女性車手,儘管為了駕馭大體量哈雷,她們的塊頭也不小,而且風吹日曬讓她們滿臉褶子,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她們同樣抱有對獨立、自由和夢想的追求。
徐路加 鄒浩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