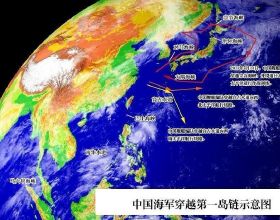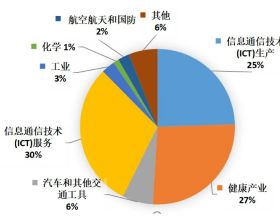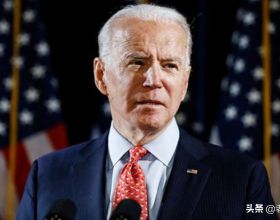獨立於濁世 的 大師
近代以來,西方勢力大舉入侵,傳統社會內部 積弊叢生,中國遭受巨大危機。有識之士開始質 組疑傳統社會的價值體系與思想學說,伴隨著救國 救民之路的探尋,批判也日漸犀利。
例如,青年時曾飽嘗家庭倫理之苦的譚嗣同 痛陳:“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因化“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為率、取便已故也”。此外在他看來,“五倫”唯有朋友一倫最為平等,其他皆屬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譚嗣同疾呼“沖決網羅”,就是希望人們打酸舊的、腐朽的社會關係,培養獨立、自主、大無畏的豪邁人格。
章太炎在當時也是如此。他指出:“小群,大群之賊也;大獨,大群之母也。“大獨必群,群必以獨成。呼籲人們擺脫傳統社會里各種束縛人心的倫理關係,擺脫種種名位與金錢的誘惑,面對濁世、雖千萬人吾往矣,同時以救世之心,重建社會組織,讓人與人之間能真正團結,形成“大群”,即近代民族國家,使中國步入獨立富強。
但改造社會,談何容易,不但要覃思精研,探索救國之道,還要面對各種困頓和誘惑。章太炎1903年對好友吳君遂感慨,教育原理,應“全學社中宜譭棄一切書籍,而一以體操為務。如是三年,其成效必有大過人者。”因為傳統舊學,不足應世變西方新學,又成為博取利祿的終南捷徑。青年學子“知識愈開,則志行愈薄,怯葸愈甚”。許多留學日本者,“當其始往,豈無穎銳凌厲者,而學成以後,則念念近於仕途”。如此焉能指望彼輩為國盡瘁。
因此章太炎1906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演說時,特別指出他心目中的自立之道。在他看來,世間驚世駭俗之論,往往出之於瘋子,而且也只有瘋子,才能言行一致,不畏險阻,實踐所言,世間能成大業者,多出自此輩。若是所謂的“正常人”在種種阻礙面前,絕難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因此他十分願意別人稱他為“瘋子”“神經病”。世人常稱章太炎為“章瘋子”,便是出自這裡。
在他眼中,“瘋子”“神經病”就是能不懼艱難險阻,不被名利誘惑,意志堅定不屈,具有勇猛奮發精神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艱鉅的革命事業裡有所作為,才能稱之為真正的獨立。
而在章太炎看來,傳統儒學遠不能塑造出這類人物。他認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堅苦卓勵者絕無,而冒沒奔竟者皆是”。基於此,他希望“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他所謂宗教,乃是具有“依自不依他”性格的華嚴、法相二宗。“要有這種信仰,才得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幹得事來。”同時他表彰長期被視為儒門異端的《禮記》中的《儒行》篇,發揚其近乎俠道的慷慨激越之氣,提倡“知恥”“重厚”“耿介”“必信”四種品德
新文化運動之後,傳統社會組織日漸解體,許多青年學子與知識分子聚集於大城市之中,他們的生活方式較之往昔,已大不相同。當時一位青年人寫道:“在街上,紅色的,紫色的,黃色的,灰色的,高階人群的海。這都市的繁華面,行走著威風凜凜的官僚政客,挺挺的大腹賈,蛇頭鼠眼的密探。
章太炎晚年也耳聞目睹世風時局種種亂象,但他不像許多人那樣,將這些現狀歸結於中國傳統不適應西方政治與文化,進而開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視此為中國歷史演進中各種消極因素交織而成,在今日湊合呈現的結果。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學的重要性。在章太炎看來,今日提倡“修己”之學,實為亂世裡的救急之術,而非藉此修身成德,優入聖域。因此他一反晚清之時對王學的批評,開始表彰後者的積極作用,認為服膺王學能使人一介不取,身處汙世而有所不為,此乃居於今世所最應提倡者。此外,他指出《大學》《儒行》《孝經》《喪服》四部經典,在文章與演講中對之極力宣揚,希望能讓人們行有操守,剛毅英勇,超脫流俗,同時不忘故常,以禮持身,從敬宗收族出發,循序漸進,臻於對民族國家的熱愛。而在“治人”方面,他主張應從中國歷史本身的演進中來認識現狀,並且目睹當時國步維艱、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因此在許多場合提倡讀歷史,視此為致用之道。他主張讀史應識大體,熟知歷代政治社會變遷,以及疆域沿革梗概,透過對於歷代史事的稔熟於胸,能夠從中吸取足以為當下所借鑑與取法之處。1936年6月14日章太類病逝於蘇州。幾痛個月後,身染沉痾的魯訊寫下《關於太類先生二富此事》一文、紀點這位曾經的老師。在文中普迅說:俄"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重在比在
學術史上還要大"他稱章太類:“以大助章作謝的墜,臨總統府老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潤心書、並世毛第二人,七次追捕、入牛獄,而革命之志,熊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智的精神、後生的楷範。”高度盛讚章的革命事蹟。
雖然魯迅最後與老師章太炎在對社會的認識與解決之道上產生了巨大分歧,他們後來基本已不相往來,但“瘋子”與“狂人”的精神,卻永不磨滅。當面對世俗的漠視嘲諷、無人理解時,當身處困境而四面碰壁、蹇蹇獨行時,是深感無助面氣餒,還是不提險阻而奮發,先哲精神不朽,願與世之有心上進責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