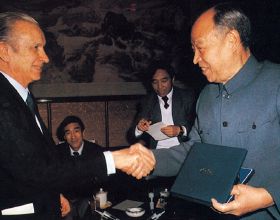西路軍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祁連山區被馬家軍衝散後,我們八百多人便組成兩個支隊,共編成六個隊,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同志組成的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經過三四十天的艱苦跋涉,終於向西衝出了冰雪封凍、荒無人煙的祁連山區。但在安西西關又被敵人兩個團圍困了,戰鬥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從敵人駐紮的村子中間衝了出來,涉過了剛解凍的安西河後,繼續向西前進。
這裡是一望無際的戈壁,走三步,退一步,真是太艱難了,但這天夜裡我們仍然走了九十里地,黎明時分到了只有九家小鋪的白墩子。各班剛吃完了用洋磁盆子煮的飯後,就聽說馬回子的騎兵又追上來了,於是不得不拖著十分疲勞的兩腿往前走。
這天我們第二支隊走在後面,走不到十來裡,敵人騎兵就追上來了,我們採取交替掩護轉移的辦法,邊打邊走,穿著草鞋的兩條腿怎能跑得過敵人釘了掌的四條腿呢?不久敵人已分成兩路從我們左右兩側包抄過來,不過並未敢輕易向我靠攏,只在兩裡外亂打槍,死死地纏住我們。
下午,敵人趕來的越來越多,幾乎已將我們的整個隊伍包圍起來了,於是開始向我們猛烈地衝擊,我們這長長的疲睏的隊伍突然被敵人騎兵衝成三個大群。這一來每一大群裡都必須獨立採取掩護方法轉移了,我所在的隊伍屬於最後的一大群。
這一大群,不久又被衝成兩個小群,我帶領的機槍排是最後的一小群,排裡有兩挺輕機槍和九支步槍,一個機槍射手不幸中彈犧牲了,我親自拖起機槍邊打邊走。敵人想徹底把我們沖垮,一直沒放鬆地向我們衝擊,我已來不及臥倒架機槍射擊了,便端著機槍橫掃。還好,戰士們都是在長征中久經鍛鍊的勇士,在這種情況下並沒慌張,已經衝到跟前來的十幾個敵人仍被我們打退了。
但情況越來越嚴重,時間再長一些,整個部隊就會更亂了,幸好這時黃昏將近,離紅柳園子還有十多里地方有一座小山,部隊便猛地向山上收縮,總算把插入我們中間的敵人擠了出去。
部隊收縮在小山後,上級就決定在這光禿禿的山頂上堅持到天黑,天黑前,敵人在迫擊炮掩護下,曾發起了幾次衝鋒,但都沒成功,我指揮的機槍排十多個人就在這山頂上崖邊,向下監視著。
打著打著,一些同志睡著了,直到晚上轉移時,我才把他們叫醒起來,有一個戰士仍坐在地上,雙手靠膝捧著頭,睡著不動,當我走去拍他起來走的時候,才發現他不知在什麼時候胸部已中彈犧牲了,排裡還有一個同志頭部負了傷,我們為他包紮好後,就跟著又前進了。
天寒地凍,夜晚部隊走得很亂,從山上下到平原沙地上時不久,又響起馬蹄聲,槍聲,喊殺聲,喧嚷亂成一片。敵人騎馬揮刀,在我們人群中橫衝直闖,許多戰士在沙地裡躲避敵人的衝殺,轉了幾個彎,迷失了方向,走在我們前面的都反而向我們跑來,隊伍更亂了。
我忙命令我排的戰士緊緊跟著我,不準亂跑,敵人殺來,立即臥倒,躲著馬蹄,等敵衝殺過去,再起來跑,我怕跑錯了方向,便沿著電線杆一直向西跑。中間又遇到了成群敵人三次攔路衝殺,第一次過後戰士們還是緊緊地跟著我,可是第二次衝殺過後,我身邊只有一個戰士了,我怎麼樣喊他們也是無用了。
在這樣的夜晚,到哪裡去找呢,四周只能聽到馬蹄奔騰的聲音。躲過第三次敵人的衝殺後,我身邊唯一的一個戰士也被衝散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之後,每隔三兩分鐘都會遇上一次敵人騎兵,敵人仍揮舞著戰刀,在這深暗的沙原上橫衝直闖,時時還向天空放槍吶喊,可在這樣的天黑夜晚,他們始終也沒把我抓住。
我躲閃地跑,身上那件打甘南繳獲來的灰大衣也被汗水溼透了,胸腔累得好像快爆炸似的,咽喉也乾燥得著了火,我仍堅持著奔跑。在快接近紅柳園子的公路旁,突然幸運地碰見了一個水坑,管它是什麼水,我衝下去捧起就喝,呼啦啦地喝了個痛快才起來。
可是這時,肚子又馬上餓得難忍,全身痠軟得說什麼也跑不動了,然而我知道這裡是停不得的,於是就大膽地沿公路走去,眼見前面不遠黑糊糊的一片,像是山,我想跑到山上去躲一躲,隨手在身上摸一下,帶的乾糧和火柴一點也沒有了,又考慮到天亮敵人定要來搜山,那就可能被敵人俘虜,不行,必須在今天黑夜逃出敵人的包圍,早點到新疆去。
我便咬著牙忍受著周身的疲憊繼續沿著公路向西走,忽見前邊有一匹馬站在那裡,身上也不知馱了些什麼東西,這真使我喜出望外,也顧不得判明情況,忙上前去把馬身上的東西弄掉,騎上就跑。
公路沿地勢漸漸地向山上爬去,我剛跑到山下不遠,就聽得半山上有人在說話,煙火的光更是顯眼,慌忙勒馬靜聽,奇怪,其中有個人的聲音似乎十分熟悉,或許是自己人,於是我就大膽地向山上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對方似乎驚住了,回問:“你是什麼人?”我一時也難回答,對方接著又連問幾聲:“你是什麼人?哪部分的?”我一聽心裡似乎更有些把握了,於是乾脆地回答:“二支隊的。”並接著反問他是哪一部分的,對方回答是一支隊,我還怕不太準確,反問道一支隊隊長是誰,對方停了一下似乎笑著說:“一支隊長就在這裡!”
啊!這時我想起剛才那熟悉的聲音,原是我們的副師長楊學坤同志,於是高興地拍馬上去,他們一共十一個人,我們隊的政委也在那裡,他們問我後面有什麼情況,我說天黑看不到什麼情況,好在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匹馬,於是我們就一起沿著公路向西闖去,這夜我們似乎沒讓馬停一會兒,天亮前就到了大泉。
在大泉飽餐了一頓,並餵了馬,雖然已疲倦得不得了,但也不敢休息又上馬趕路了,我們這孤零零的十二個人,身上的衣服各式各樣,長皮衫短皮襖,敵人的藍軍服,大衣,所騎的馬的裝束也不整齊,有鞍馬,有光背,好久沒有理髮了,頭髮鬍子長得特別長。
沿途老百姓都把我們當成土匪,見了我們都害怕,我們在甘南打土豪時得來的金梳子、戒指、洋錢,統統拿出來請老百姓煮點吃的,要多少錢,給他多少錢,當然不管怎麼疲倦,吃了飯立刻加鞭趕路。
雖然我們身上都帶有短槍,但仍不免有些膽戰心驚,見到一支駱駝隊也得先派人前去偵察好後才敢前去。馬跑一陣又走一陣,絕不讓它偷懶,當天中午到了馬連井,下午太陽還沒落山,就趕到了新疆邊境上的星星峽山下。
只見山上新疆邊防軍哨兵的刺刀閃閃發光,峽口兩邊山峰陡峭,雖然早就知道他們是在蘇聯幫助下裝備起來的,而且口號也是“革命”的,但到底還是初次見面,也難完全相信,想了想,還是先派了個人上去聯絡了以後,才一同走了上去。
他們是一個什麼主任來接待的我們,很熱情,口稱他早就來這裡等著迎接我們了,給我們煙、茶,安置休息吃飯,還問我們大部隊什麼時候上來,我們當時只好裝著說,我們是先遣偵察隊,大部隊不久就會上來。
夜裡我們正睡得甜的時候,忽然那位主任把我們叫起來,把盛世才給他的電報念給我們聽了,說是駐在哈密的姚司令率部叛變了,要借送軍火物資的名義來繳紅軍的槍,投降蔣汪。盛世才叫他堅守住星星峽,等候部隊空投增援,可守衛在星星峽山的只有一個排,兵力實在薄弱,因此請求我們這支“偵察支隊”援助,我們當時答應了,也顧不上休息,就連夜與他們的四十多個人,共同守在峽後的兩邊山上等著叛軍。
叛軍當夜並未到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開來一輛裝著爛棉被等物資的六輪卡車,裡面有一位副官,我們當場逮捕了他。正如昨夜盛世才的電文中所說的一樣,這位副官是先前來試探情況的,叛軍不日即會向這邊打來。為了不使敵人直逼到星星峽來,第二天清早,我們就同他們的兩個班乘上那輛卡車趕到若水去設伏,在半山上等到下午,叛軍果然乘著汽車和戰馬揚長而來。
在半山坡上我們首先打毀了他們走在前面的一輛卡車,隨即向敵群猛烈掃射,奇怪,叛軍沒多會兒突然衝哈密方面縮回去了,大概是他們知道陰謀已經敗露,又不清楚紅軍目前的底細,輕舉妄動也未必妥當,因此不如趕快回去守住哈密為妙吧。
這天黃昏,我們凱旋地回到了星星峽,這時李先念等同志已帶著八十多位同志來到星星峽了,他們並沒有沿公路來,而是在紅柳園子以北插入山區後,再向西插到這裡來的,我們這十二個散兵,總算又回到了紅軍大家庭裡來。
往後天天都有我們的人向這裡跑來,一天三個兩個十個八個,十幾個,不久我們的隊伍又有四百多人了。在星星峽住了兩週多,哈密之敵基本上已平定,盛世才從迪化派出一個大隊,黨中央派陳雲、滕代遠同志帶了一批汽車來到了星星峽,把我們全都接到了迪化。後來,我們又從迪化來到了延安。
王正國同志簡介:(1918年——1968年),四川省通江縣周子坪村人。1932年底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翌年加入共青團,1934年4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歷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269團特務連班長、269團3營排長、267團2營6連指導員。1936年10月任三十軍保衛局偵察科員,10月中旬調到263團任副特派員,12月任263團5連指導員。參加了浴血奮戰的長征“西路軍”戰鬥於1937年3月底到達新疆星星峽,1937年3月~1940年2月在新疆完成了炮兵的系統學習。
1940年2月返回延安,擔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1連連長,10月任3連連長。其時獲軍委頒發的“勞動英雄”獎章和“神炮手”獎章。在延安炮校任5大隊隊長兼教員。1945年11月任晉察冀軍區炮兵團副團長,1947年5月任炮兵3團團長。1947年8月奉命調任華東野戰軍特縱炮1團團長。1949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第三師副師長。
1952年8月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深造。1954年12月調任炮七師師長。1957年到宣化炮院進修,1959年底畢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畢業體檢時突發疾病,未分配新工作。1964年中央軍委任命為北京軍區炮兵副司令員,因病復發未能到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