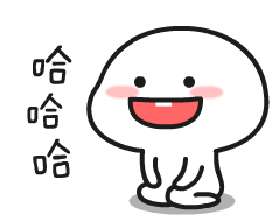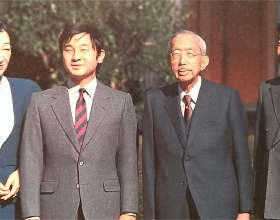畢大費/編撰
本文共約8900字,其中包括日軍侵華時期大量親歷的真實史料和資料,讀完約需20分鐘。
1917年2月,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者,29歲的約翰·本傑明·鮑威爾,受到朋友湯姆斯·密勒邀請,隻身來到上海,擔任滬上知名刊物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筆和發行人,同時,長期兼任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
1931年之後,日本在華活動日益猖獗,鮑威爾多次秉筆直書日本人在華的種種惡行,被日方列入重點名單。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日軍佔領上海公共租界,《密勒氏評論報》隨即遭日軍查封。12月20日鮑威爾在都城飯店(今上海黃浦區江西中路180號)寓所內被日軍逮捕,關押在虹口北四川路大橋大樓(今上海市虹口區四川北路85號)改建的監獄,獄中遭受非人待遇,雙足罹患嚴重的腳壞疽,不能行走。
1943年,鮑威爾作為日美交換戰俘,乘船返回美國。康復治療期間,撰寫了個人回憶錄《我在中國的25年》,時間跨度即為1917年-1943年,記錄了許多他所親歷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由於被日軍囚禁時健康遭到嚴重損害,1947年2月28日,鮑威爾在華盛頓去世,時年59歲。
前不久,我剛剛讀完該書,感觸頗深。作為一名長期在華的美國人、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一位侵華日軍的直接受害者,鮑威爾獨特的視角、敏銳的觀察、細膩的敘事,以及悲憫的文字,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和洞察侵華日軍的罪惡行徑。
本文有關日本在華經營“黃賭毒”的相關內容,【1】【2】【4】全部摘自鮑威爾的這本回憶錄(譯者:劉志俊)。為了使摘錄文字獨立成篇,便於展示同一主題,也便於讀者理解,相關段落與內容已做調整。所有小標題均由我新增。
【1】日本人在華製毒販毒
1937年,日本在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州區)成立冀東傀儡政府,將當地的中國警察和海關人員全部驅逐出去,從此,這個區域的走私、販毒活動異常活躍。
6月初,我抵達天津時,有一個“神秘屍首”案,正在引起當地居民普遍關注。據當地報紙報道,已有107人在海河中遭遇不測。海河流經天津,最終注入大海,隨潮水的漲落而不斷變化。這107個人全部是男人,年齡自20歲到40歲不等。從屍體看來,這些人在遇難前,肉體上並沒有受過任何創傷。
為探究這起神秘屍體案的內幕,我前去當地警備司令部進行採訪。期間,我察看了許多由相關人員提供的照片,它們記錄了來自海河中的屍體。一張由六個屍體勾勒成的照片最先引起了我的注意。從這張照片中,我發現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他被從海河撈起來時還有一息尚存。照片上,這個人的頭部露在海面上,由此推斷他可能是自己滑落或被人扔在一個淺水區域。當時,有人將這個人送抵醫院,經過緊急搶救後,神智得以清醒。之後,這起神秘屍體案最終揭曉。這個人就是賈永濟(譯音),這個案件發生時,他才30歲。
賈永濟是海洛因的吸食者,毒癮相當厲害。賈永濟說,他記得他與一大批農民工從中國內地出發,前往日本租界一個供人休憩的地方。那裡滿是海洛因和鴉片,人們可以隨意享用。他曾在東北工作了三個月時間,並將薪水全部積攢下來。他的口袋之所以沉甸甸的,就是因為裝著這些為數不少的錢。不過,從海河裡打撈他時,他身上未穿任何衣服,更別說口袋裡的錢了。賈永濟還說,他從一個女孩那裡購買了一些香菸,這些香菸裡或多或少都有海洛因——這是他所能回憶起來的最後事情,至於其他事情,他沒有印象了。
日本人曾在天津日租界裡經營著許多毒窟。有關當局對神秘屍體案展開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從海河被打撈起來的人可能就是在這些毒窟裡遇難的,可能還有少數人死於海洛因和鴉片。與這個神秘屍體案有關的屍體,多數都被捲入滔滔大海中,因為海河在漲潮和落潮之間形成巨大的力量。當時,外界散佈著這樣的訊息:在天津日租界警察的指示下,卡車時常出沒在街頭巷尾收集犯毒癮的人的屍體,而後將這些屍體運抵河岸,趁潮漲之際,將這些屍體扔向河邊,之後這些屍體被海潮捲入大海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街頭巷尾聚集著許多日租界毒窟。這些犯毒癮的人難免還有些氣息,不過在收集屍體時,日本警察根本不顧及這類情況,依舊按死屍處理。每逢冬天,天氣漸漸變冷,海河隨之結冰,日本警察為把收集的屍體扔到海河裡,時而在海河上鑿冰窟窿。
有關方面揭曉神秘屍體案後,便將之公佈於眾。此後,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特地組建了一個招待所。這個招待所雖然有點兒廉價,但在關外的農民工重返家園前可供他們臨時歇腳,這正是政府成立這個招待所的目的。我專門走訪了這些招待所,採訪了許多人,獲知招待所的勞力多數都吸食過日本的海洛因。自日本人在上海日租界販賣海洛因以來,原本抽菸片的中國有錢人競相改為吸食海洛因。
當時,中國人主要透過液體和固體這兩種途徑來吸食海洛因。前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加入注射液後,將注射針插入手臂的面板之下;後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粉末捲入香菸後,吸毒人開始吸食。我還採訪了一些劣等的海洛因交易和吸食場所,期間發覺一些年紀輕輕的中國人購買小包的海洛因。按美元計算,這些白色粉末的成交價大概是一角或兩角。之後,這些中國人在抽出25%的菸絲後,將這些白色粉末倒入香菸中。在傾倒時,他們將香菸呈45度傾斜,以免這些粉末漏出來。接著,他們將香菸點著,進行吸食。為此,日本專售海洛因的販子開始銷售吸菸架。從外表上看去,這種吸菸架頗似高腳杯,為採用香菸進行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這種海洛因的吸食法被中國人稱之為“打飛機”。
日本海洛因製造廠不僅分佈在天津,還分佈在大連。這兩個地方的海洛因產量日益增多,當地的工廠也日益興旺和強大起來。與此同時,鴉片的供給充分,足以滿足吸毒者的需求。正因為這樣,日本人還開辦了一系列店面,方便喜歡抽鴉片的中國人前來享用。這些店面包括一個大賓館,賓館的外表富麗堂皇。不過,賓館裡面的設施相當土氣,除了一個僵硬的枕頭,就是木板或木床。顯然,賓館裡原本的好傢俱都被撤走了。從外表看來,這些木板和木床廉價得很,上面平鋪的是草墊子。
這家賓館的中間有一條通道,雖然狹窄,卻為吸毒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客人順著這個通道爬,可以抵達任何一個空床或無人的長凳子上。前來光顧這家賓館的顧客,多數是成對出現的,一對男女搭檔的情況居多。男女搭檔進入賓館後,便躺在木板床的草墊子上。需要指出的是,他們面對面躺著,抽菸片的器具全放在兩人中間。之後,一個女服務員帶著兩支鴉片煙槍、一個小酒精燈和一個小盒子前來。小盒子的種類有兩種:一種是洋鐵皮盒,一種是瓷盒。鴉片煙膏便裝在小盒子裡,它的模樣酷似濃濃的黑糖蜜。
通常情況下,這裡的女服務員是朝鮮人,年齡要麼是10歲,要麼是12歲。接下來,這個女服務員順手拿起鐵釺朝小盒子中間插去,扭轉幾下之後,只見鐵釺的一端挑起了一塊小小的煙膏。這個鐵釺的外表很像一根大針。接著,女服務員將這塊煙膏置於點燃的酒精燈上方燒著,她翻轉煙膏的速度相當快,僅僅為了防止將煙膏點燃。鴉片煙槍槍頭鐵鍋上有一個小孔。煙膏一旦冒煙,這個女服務員就將插著球狀煙膏的鐵釺移離火焰,放入這個小孔內。抽鴉片的人隨即將鴉片煙槍移至酒精燈上,開始吸食。只見這塊煙膏開始燃燒,抽鴉片的人深吸一口氣後,一股濃香的鴉片煙味瀰漫開來。自然,抽鴉片人的肺部也充斥著這種煙味。如此這般,吸食鴉片的人連續抽了兩三個煙泡,直至在不知不覺中昏睡過去。抽鴉片的人每次吸食鴉片的數量是一管煙,或者說是一袋煙。按中國銀元換算,吸食人每次需要支付的金額是1元。顧客倘若讓鴉片買賣場所的女招待陪同抽鴉片,那麼需要額外支出中國銀元4元。
天津日租界的一條主要道路是朝日路,我走訪的鴉片場所便位於這條街上。這家鴉片場所是一棟六層高的賓館,每層設有20多個隔間,每個隔間設有木床,可供10~15個人同時抽鴉片。自然,在這樣的房間裡,顧客是沒有隱私可言的;前來關照的顧客也沒有想隱瞞東西的意思,更別說是任何秘密行動了。這家賓館全天營業,房間裡的燈整天亮著。在燈光的照耀下,每個房間的客人貌似始終處於白天。當數以百計的顧客同時吸食鴉片時,煙槍中燃燒的鴉片煙泡的味道可以瀰漫至朝日街附近的街道上。
當時,在日本租界裡,抽鴉片和吸食海洛因的中國人相當多,甚至到了天津政府無法控制的地步。為此,天津當局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在日租界附近的中國區域,無論是鴉片和海洛因的吸食者,還是這兩種毒品的出售者,一旦被抓住,等待他們的將是死亡的下場。乍一聽,這種措施相當地苛刻。然而,中國人為緝毒而作的這種鬥爭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與日軍手中的步槍相同的是,鴉片、嗎啡及海洛因也是日本人向中國滲透的工具。需要說明的是,嗎啡和海洛因是經鴉片提煉而成的。在日本,有關當局是明令禁止吸食鴉片的。然而,日本當局卻多次煽動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和朝鮮人在日軍進佔的亞洲地區進行鴉片交易活動。
鴉片煙的買賣活動很大程度上與日軍有關。倘若日本不爆發自清的革命運動,那麼外界是無法獲知這一點的。當時,除嗎啡製造廠外,天津和大連還有海洛因生產廠。日軍特務處直接經營著這兩大工廠,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除此之外,日軍特務處還經營著上海的鴉片煙館和與它關係密切的賭場。)
【2】日本人在華經營賭場
種種跡象表明,在日軍佔領上海後(筆者注:指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好像就出現了一支專門搶掠的隊伍,一方面要榨乾上海市民口袋裡的錢財,一方面不斷地摧毀上海市民的道德規範。
1939年初,我曾在做過一項調查,調查物件是上海公共租界地區的賭場和煙窟。那時候日本軍隊雖然尚未將租界佔領,但已經控制了上海華界。調查結果顯示:自從日軍來到上海後,已經新出現了125家賭場和煙窟。這個人口眾多的區域,受一個簡稱為“3S”、隸屬於日軍戰鬥部隊的“特別行政區”管轄。這與美國任何一個大的、正在不斷髮展的城市郊區十分相似。這個特區與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控制的區域只隔了一條街,所以很多人都會把它與英美租界、法租界的邊界弄混。
當日本軍隊將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其他地區佔領後,他們便立即建立了附帶煙窟的賭場,這是他們建立起來的第一項“文化事業機構”。經營賭場的人,要麼是日本浪人和強盜土匪,要麼是中國的地痞流氓,還有就是自稱汪精衛組織中的人員。後來,日本憲兵曾想封閉所有的煙窟,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有些不像話。不過,他們並沒有成功,因為日軍“特別行政區”人員非但阻止他們這樣做,還專門成立了“上海特許娛樂部”來管理賭場。於是,上海出現了大量的大煙窟、賭場、妓院及海洛因戒毒所。
這類場所中的大部分每年都要交十分昂貴的管理費。除此之外,屬於“皇宮”一類的高階場所,每天都要交500美元的稅,那些中等的也要交150美元。不管這類場所位於哪裡,每一個場所的牆上,都貼著非常引人注目的宣傳海報,而那些富麗堂皇、裝修豪華的場所卻與之相反,什麼也不貼。
每一個煙窟和賭場,都會召集下等社會里的打手作為保鏢。敵對賭場的打手們,經常暴發衝突,甚至進行暗殺,因此,每當夜幕降臨,大街上就籠罩著一層陰森恐怖的氣氛,根本沒有人在街上行走。有一家名為“好萊塢”的豪華大賭場,公然對外宣稱,在汪精衛偽政權控制區內,共有400名武裝保鏢。如果兩家賭場的保鏢發生衝突,場面就會像一場小規模的戰爭那樣激烈。
後來,大量賭具突然出現,並散佈到上海市的每一個角落。人們都想知道這些賭具的來源,但一直不得而知。後來,大家才知道了真相:一位日本商人專門開辦了一家制造番攤、骰子、輪船賭等賭具的製造廠;此外,他還從位於廣東與九龍交界處的大賭場買來了大批現成的裝置,那裡具有很多生意興隆、歷史漫長的大賭場。所有這些大賭場,無不自稱為汪偽政府下的附屬機構,後來便勾結日本浪人,來到上海經常煙窟和賭場。
經營賭場和煙窟需要房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人強迫西洋人搬到其他地方去,用西洋人的房屋作為經營場所。可實際上,這些洋人們的住宅根本無法用來開賭場。於是,一幢幢簡陋的房屋接二連三地被修建起來。這些新建的房屋,大部分格局都是相同的,中間是用來當作賭場的大廳,四周是用來當作吸食鴉片的煙窟的小房屋。
一直以來,賭博、買賣和吸食毒品都會遭到公共租界當局的禁止。因此,這些賭場和煙窟的建立,立即就讓上海老百姓感覺到,他們有很多機會可以做這些壞事,而且無須再擔心警察橫加阻攔。有一小撮不受其國家領事官員治外法權所管轄的西洋人,也開始經營起賭場來。不過,這些西洋人很快就發現一件事:他們經營賭場,時常與日本人發生衝突。日本人不希望,也不想允許歐洲人經營這類罪惡事業。有一位名叫裘法蘭的匈牙利人,有一段時間,在上海西部地區經營了一家非常豪華的賭場,可後來由於沒有與日本軍部搞好關係,遭到了日軍的制裁。日軍將其逮捕,之後將其關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的政治犯監獄中。由於無法忍受監獄裡的生活,這位匈牙利人就在監獄裡上吊自殺了。
【3】日本人在華經營慰安所
本節內容摘自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及其團隊所著《證據:上海172個慰安所揭秘》,同樣,為了便於展示同一主題,便於讀者理解,相關段落與內容已做適當調整。
上海是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軍在海外最大的基地。為了給海軍陸戰隊官兵提供“衛生”的性服務,早在1931年11月,日本駐上海海軍當局已將虹口一帶的“大一沙龍”“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等4個日本僑民經營的風俗營業酒吧,指定為海軍特別慰安所,不僅要求其對日本軍隊開放,還要求其接受軍醫的身體檢查。這是慰安所名稱的第一次出現,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此後,“大一沙龍”慰安所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長達14年。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所謂“慰問戰地官兵”的女性,並未見有被稱為“慰安婦”的,她們往往被稱為“賣春女”“酌婦”。“慰安婦”一詞正式的使用,約見於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以後。後來擔任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的岡村寧次,此時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正是他,為了維持日軍敗壞的軍紀,首次要求日本關西地區的行政當局招募日本婦女,集體來滬“慰問”日軍,他採用了一個好聽的名詞—“‘慰安婦’團”。1932年3月“‘慰安婦’團”登陸上海,並在吳淞、大場、江灣等地為日本陸軍服務,這是日軍第一次使用“慰安婦”一詞。從此以後,“慰安婦”的身影,便開始遍及日軍鐵蹄踐踏之處。當“一·二八”事變結束之後,日軍“‘慰安婦’團”雖返回了國內,但日僑、朝鮮僑民經營的為日軍服務的慰安所卻不斷增多。
1937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全面發動以後,日軍佔領上海。戰爭初期,日軍設立了上海派遣軍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楊家宅慰安所”。這是一個知名度非常高的日軍慰安所,一方面,它的許多制度如“慰安所規定”、價格等成為後來日軍慰安所的範本;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軍醫麻生徹男拍攝的照片和記錄,留下了真實的史料。此後,日軍直營的,日僑、朝鮮僑民經營的以及漢奸經營的各種慰安所充斥上海各處。
在上海,有些地區的慰安所是非常集中的。作為進入上海的第一鎮吳淞扼長江之險,駐紮有大量日軍,據我們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多年的調查,前後至少有17家慰安所在那裡出現。日軍第13軍司令部設在江灣五角場(其址在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其周邊的慰安所十分密集;江灣萬安路戰時被日軍稱為“花街”,有慰安所6處。四川北路周邊是日本僑民活動的中心地帶,是慰安所最密集的區域,共計有70處以上,包括橫浜橋美楣裡的9個慰安所和松柏裡一個弄堂的8個慰安所。
為了加強對慰安所的管理,日本統治者還設立協會來進行管理。1940年2月,上海虹口閘北區慰安組合會成立,此會的成立,是由偽閘北區公署日指導官嘉野正孝將成立報告遞給偽市警察局日指導官秋山健次核准的。該會設組合長一人,由與日人關係密切的原妓院老闆何乾賡為組合長,並配有為妓女體檢的醫生和進行有關事務調查的調查員若干名。會址設在虯江路95弄2號,並訂有13條慰安所臨時規約,除規定慰安所的適用範圍為閘北區,由偽警察局管理等外,還特別強調衛生管理,例如第5條:妓女每月須經本會指定醫師檢驗3次,確定無花柳病者,始準營業;第6條:慰安所內裝置必須清潔衛生,置備消毒用品,等等。
日軍在上海設立了多少個慰安所呢?經20多年的調查,我們在《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首版時統計為149家。該書出版後的近半年裡,我們陸續查訪到一些新線索。新增加的有乍浦路254弄慰安所、乍浦路180號月迺屋、武昌路338號孔敦經營的慰安所、中山南二路的“徐家宅”慰安所、今“龍山新村慰安所、泖港鎮慰安所、崇明縣城慰安所等,增加了不少,目前所知的上海日軍慰安所為172家。
日軍慰安所按其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可以分為多種型別。
第一種是日軍自己經營的,日語用“軍直營”來表示。如1938年1月設立的楊家宅慰安所(地點在今楊浦區翔殷路東沈家宅),由日本上海派遣軍東兵站司令部設立。日軍佔領上海初期,設立過一些搶抓中國女子為性奴隸的場所,在虹口地區設立的“行樂所”等也屬於此類。“八·一三”會戰以後,日軍佔領了杭州路、眉州路一帶作為軍營,最初駐紮的是千田部隊。在現在的躍龍化工廠門口的位置,設立了“千田部隊慰安所”。後來深谷部隊入住於此,於是,該處又變成了“深谷部隊慰安所”。
第二種是日本僑民根據日軍命令設立的民營慰安所。號稱海軍在滬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就是退役海軍士兵坂下熊藏奉海軍之命令開設的地址在公平路公平裡,他兒子筆名為華公平,就與此有關。“海乃家”慰安所的房屋、開辦費用、所需物品等均得到日軍的大力支援,甚至連“海乃家”三個字也是由日本海軍方面確定的。江灣萬安路、四川北路等是日僑經營、管理的慰安所的集中地。包括對外以其他面目出現的慰安所,如岸本忠治經營的“風月莊”,地址施高塔路(今山陰路)花園裡17號,對外的名義是日式普通旅館,實際上也是日軍慰安所。此外,還有以食堂、酒吧、舞廳等名義出現的慰安所。
第三種是朝鮮僑民在日軍的指使下設立的。這些慰安所多以酒吧、舞場等名義出現,尤其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頗成規模,許多朝鮮女子就是被控制在這樣的慰安所遭受凌辱的。
第四種是日軍或日本人指使偽政權或脅迫中國妓院主開設的。這類慰安所多出現於1938年以後,有的名慰安所,有的則稱妓院。
為了管理慰安所,經過偽上海特別市政府警察局、偽上海特別市衛生局批准,虹口閘北的慰安所公會於1940年設立,該會制定規約。規約規定,開設慰安所者需提供申請書,由閘北區警察署發給許可執照。
關於上海“慰安婦”的人數,我們可以從慰安所規模和日軍人數兩個方面進行考證。
上海慰安所172個,每個慰安所的“慰安婦”以平均20人計算,但虹口的大型慰安所一個所的受害者達千人或數百人,估計“慰安婦”人數約6000人,以更替率4.0推算,總人數約24000人。
再從日軍士兵人數與“慰安婦”之比例來分析。以1945年日本投降時,上海受降日軍為165000人計算,以“慰安婦”與士兵比例1:29推算,“慰安婦”應該為5689人。由於疾病、逃亡、死亡等原因,更替率4.0計算,得出“慰安婦”人數為22756人。再加上短期停留上海的日軍部隊所需要的“慰安婦”,上海“慰安婦”總人數可能24000人以上。
根據推斷,中國受害者仍是最多的,而朝鮮“慰安婦”的數量,也應該比日本受害者要多。推斷的數字是,在上海的24000名“慰安婦”中,中國“慰安婦”約有12000人左右,朝鮮“慰安婦”約7000人,日本“慰安婦”約為5000人。
【4】日本人在華經營慰安所
關於上文【3】提到的日本籍慰安婦,據鮑威爾《我在中國的25年》一書記述,1935年他曾赴日本採訪,專門記述了一段有關日本藝妓的文字,便於讀者對相關資料進行參考驗證。
日本北部地區處處顯示出不安寧的跡象,一方面是由於農作物產量普遍大幅度地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為當地政府依舊徵收沉重的賦稅。有一些掮客,專門從事買賣人口的勾當,除村鎮的小賓館外,他們還居住在一些農民家裡,這些農民處於極度貧窮的狀態。
日本鄉村的少女,不僅被這些掮客販賣到大阪的紡紗廠,還被販賣到藝妓館。這些藝妓館不僅分佈在東京等日本大城市,還分佈在中國東北的城市中。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大批日軍進駐中國東北城市。這些少女都是經她們父母之手賣出的,不過被賣出前,她們的父母要與這些掮客簽訂一個契約。通常情況下,契約在三年內有效。
不過,日軍城市藝妓館的門檻相當高,那裡只接受最好看的少女。倘若最好看的少女順利入圍,有關方面將預支約1500日元,相當於700左右美元(筆者注:此為1935年的兌換率)。給她的父母,權且當作是賣女兒應得的費用。為了給這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置辦服裝,掮客還需另外支出若干日元;前後費用大約在2000到2500日元之間。
此後,這個少女始終處於被奴役的狀態,直至她將所有的債款全部償還。如果一個很有錢的人相中了這個少女,那麼她就能夠迅速擺脫被奴役的地位,重新獲得自由,不過,這種情況很少見。
事實上,這些少女的命運都很悲慘,從被賣進藝妓館的那一刻起,她們一直在藝妓館唱歌跳舞,以此混口飯吃,直至容顏蒼老;那時,她們對於藝妓館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利用價值,因而被販賣到妓院,過著一種生不如死的生活。
【5】我們應該如何勿忘國恥與繼往開來
2014年9月3日,大大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將以上問題,講得很透徹,總結為“抗戰精神”,主要四點:
1、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
2、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
3、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4、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
大大說,“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是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強大精神動力。”
從講話可以知道,銘記歷史,絕不是一個空泛的口號,至少應包含三個深刻內涵:
一是我們要牢記日本的軍國主義,曾經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的極大戕害,如今,這幫軍國分子已經變身為日本右翼分子,我們應始終對這夥人保持警惕。
二是我們要牢記抗日英烈們的偉大付出,“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青天”,和平來之不易,我們應該珍惜今天。
三是我們應該用抗日精神不斷激勵自己,自強不息,共同奮鬥,用我們的辛勤、汗水與智慧,為中國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讓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悲劇永不重演,這才是我們給予抗日英烈的最大慰籍,也是我們留給子孫後代最大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