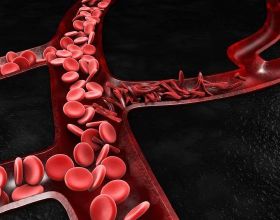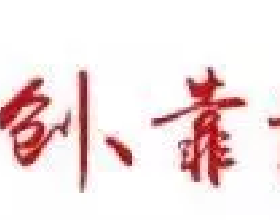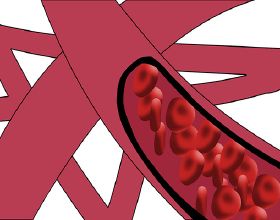王國維自沉
那一年上鹽官,我去過王國維的故居。
玻璃櫃裡陳列他的書——應該是後人整理,關於文學、美學、史學、哲學,還有考古學的,沒想到他寫了那麼多。由於年代久遠,這些書漸發黃、枯脆,彷彿一觸即碎,原來留在紙上,也一樣靠不住。
我在他的書房裡默立,那種老式讀書人的書房,自有一種氣場,讓人沉靜。壁上懸著他的一幅長衫素像,山長水瘦的,十分孤寒。他這個人,彷彿一切都是舊的,包括那副本該時髦的眼鏡。他的相貌,像個賬房先生,跟他的精神世界不搭界。
他所處的時代,跟他的所思所想,也不搭界。
我雖然對他的學術研究,知之甚少。但我知道,我的審美全來自於他。
他28歲寫下《紅樓評論》,開創了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來分析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先河;他33歲發表《人間詞話》,提出了“境界說”,革新了傳統文學評論理念;他36歲寫出《宋元戲曲史》,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戲曲發展史的專著……這樣一個開文化先河的人,於1927年6月,投水昆明湖,將自己51歲的生命定格在歷史漫漫風沙之中,既孤單又淒涼。
關於他的死,一度是讀書人的避諱。即使後來對他的研究日臻繁榮,即使後來曾經痛罵過他的,也開始恭恭敬敬地談論他,如同過去膜拜魯迅一樣,大家開始借國學重塑他的金身。但在說及他的自殺時,還是小心翼翼,神色惕然。
也難怪,比起梁啟超的維新,章太炎的入獄,胡適之的白話,熊十力的革命,他的悄然自沉,是如此不識時務。
到後來,八卦盛行,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他因人生困苦,有的說他因忠於清室,有的說他因朋友背信,還有的不無深意似地談到當時革命軍北伐的步步進逼然後舉出他死時留下的“義無再辱”說,彷彿其死因不證自明,如此等等。
所有這些談論,可說全都有案可稽,也可說全是無稽之談。說全都成立,是因為這些事因的確全都指向他的自沉。他不是幸運之人,人生裡最深重的苦痛,彷彿都被他一人佔盡:幼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妻、晩年喪子,諸如此類遭際,足夠壓垮一個人,讓人崩潰。這似乎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也同樣印證了老子的一句話——人之大患在我有身。
但把這些具體不幸,歸結為他一步步走向昆明湖的必然命運,有點想當然。
王國維的自沉,猶如賈寶玉的撒手,是基於其所有的生存境遇和總體的生命歷程。寶玉出家固然與黛玉之死有關,但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在懸崖撒手的路上,王國維亦如是。
對於王國維自沉領悟最深的,是陳寅恪。
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寫道:“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末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榮辱委瑣齷濁之說,皆不足置辦,故亦不之及雲。”
當陳寅恪將王國維定義為承擔了歷史命運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時,無疑意識到,他自己也將步入這樣的命運。這樣的命運,不是世俗之人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世俗社會可以置評的。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都具有超然於俗世的獨立不羈,所謂能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在商周之交,這樣的命運承擔者乃伯夷叔齊;在漢末黨錮之禍中,他們是李膺、範滂之輩;在魏晉時代,則是臨刑撫琴的嵇康及其同仁;及至到清一代,由曹雪芹以《紅樓夢》承擔。一個民族的文化命脈,如斯前赴後繼,宛如一縷清香,嫋嫋不斷。
那天,我在先生的書房默立,突然自卑,他寫下皇皇鉅著,我只有一本《人間詞話》置於案頭。他這個人,也許窮盡我一生,也無法真正瞭解。
李叔同出家
李叔同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一個翩翩公子;立意要做和尚,就徹底地做一個和尚。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像個青衣,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大面又像個大面……
1918年夏,他削髮為僧,文人、戲子、軍閥和革命家的茶杯摔了一地。林語堂嚇了一跳,“這個遺世而獨立的人,終於拋棄了這個時代,跳到紅塵之外去了。”
他在門前貼上“雖存若歿”,不見家人,亦不見佳人。
雪子從海上來,又長泣而去。兩人相伴多年,今日行至盡頭。
髮妻俞氏也來了,帶著哮喘的兒子,長跪寺外。他託人帶話:不見,俱往矣。
同那時的世家子弟一樣,他年少時,把那個時代所有可能的戲耍都逞性玩了一遍。唯一不同的,他把每一樣都玩到極至:詩文第一,丹青第一,金石第一,西洋樂第一。
“人生如大夢,惟我獨先覺。”他夢做到一半,突然醒了,要做和尚去。
關於李叔同為何出家,世人有幾種說法:
一說家境破敗。
他出身優渥,少時豐足。但父親早逝,母親二十四歲扶老將子,家境大不如前。有人據此提出,叔同變成弘一,必有家境破敗之因。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富貴一旦真成了浮雲,天空便鬧騰著大團大團的幻滅。
這個說法並不可靠。受康梁維新失敗影響,李家於1898年前後南遷滬上,住在法租界。那裡有李家的錢莊生意,少東家李叔同完全過著富家世子的生活,不說花天酒地,至少也是五光十色。
二說精神破產。
李叔同追隨康梁,維新未遂,革命不成,啟蒙無望,文教救國又如高原打井,儒家理想猶如水中月鏡中花。他在《金縷曲》中感念: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修齊治平,經事濟世,當真冥冥也,渺渺也。
但這個說法亦有侷限。“經事濟世”雖說冥冥也、渺渺也,但他從未放棄這個理想。出家多年之後,他持“弘一法師”的盛名和威儀資糧,發起和參與了大量護生救國運動。他做和尚,並非以出世的念想替代入世的理想。
三說靈魂生活。
這說法來自豐子愷。作為李叔同最親近的學生,豐子愷認為自己的老師跨過人生的兩級臺階,登上了靈魂的第三層,如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了無遺憾。
“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
這一對師徒,一個冷寂,另一個溫暖。後者既出世又入世,兒女成群其樂融融,而前者卻中途棄俗離家託缽,一雙芒鞋遍嘗人世艱辛。
登上高樓、到燈塔去的弘一法師,並未像蔡元培、章太炎、吳昌碩、馬一孚、潘天壽等一眾友人設想的那般,演一出才子出家的瀟灑戲文。文人親近佛教,大多偏好流水行雲、花開自在的禪宗,比如王維。玩夠了,放下了,歸隱做一個無事行者,寫幾首空山新雨後的禪詩,人也就得了大解脫。
可李叔同選擇的,偏偏是修行最苦最嚴苛的律宗。
從1918年剃度到1942年圓寂,他二十四年精嚴持戒,從無觸犯。抄書不忍寫“殺”字,坐椅子之前都要搖一搖,以免誤傷蟲蟻。兩餐茹素,過午不食,後因菜價上漲,竟連香菇菜心也不吃了。雖有弟子豐子愷、夏丏尊供養,但他每月只花幾毛錢,字寫在毛邊紙上,僧衣補了又補。
那個時代,風雨飄搖,天地晦暗,有人刀刃上舔血,有人溫柔鄉里酣臥,他在古廟裡點燈。
作者:甘草子,不小資,不文藝,不妖嬈,不風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