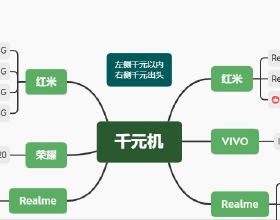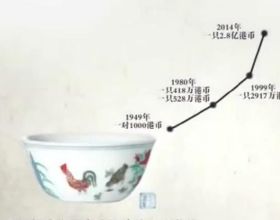在4000年前的一個夜晚,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地震、泥石流吞沒了位於青海省海東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官亭盆地的喇家村。瞬間發生的災難,將歷史永久地定格在那一刻。
在中國,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導河積石的故事家喻戶曉,而大禹所處的年代也恰好是公元前21世紀左右,所治的河水正好就是積石山下喇家村旁流過的黃河。
在喇家遺址中,無論是窯洞式的聚落形態、特殊的地面建築、聚落外圍的寬大壕溝、區域中心的廣場和祭壇,還是禮儀用的玉器、巨大的石磬、精美的彩陶和漆器、組合的生活陶器、房址裡的壁爐等,都有力地證明了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圍垣聚落,當時已經進入文明初期階段,或者已經出現了王權或其雛形。
從城市的形制來看,喇家遺址似乎驗證了芒福德“在城市的發展中,帝王處於核心的位置”的說法。中國城市從一開始就是基於“築城以衛君”的目的而建立的。不是商人而是王權促進了城市的出現和崛起。在中國,城市一出現,就具有了無可替代的政治象徵意義。
喇家遺址、宗日遺址、沈那遺址、柳灣遺址以及青海分佈廣泛、面積巨大的新石器時代古遺址,為早期中國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線索。
戴傳賢指出:“青海是中國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終於流成了泱泱大國。”
青海,早在2至3萬年前就有大規模的人類活動。高原先民先後經歷了考古學意義上的舊石器、新石器時代,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農業、定居生活在“兩河流域”(湟水河、黃河)定型,人們用雙手製作彩陶,並在高原腹地建設起最為富饒的家園,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
青海被譽為“彩陶王國”。作家張承志在《北方的河》中深情地寫道:“河湟地區彩陶流成了河。”青海樂都柳灣彩陶,無疑彙集了中國彩陶的眾多型別,代表了中國彩陶的巔峰。
與彩陶文明相媲美的是青海青銅文明。距今4000年左右,青海先於黃河流域進入使用青銅等金屬階段。青銅時代由人類社會大發展時期伴隨人類第一次大分工而出現:隨著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還有社會階層、奴隸制度、有組織的戰爭和貿易。

在同德宗日遺址中曾出土了一組骨刀叉,這組骨刀叉,跟我們現在用的西餐刀叉勺形狀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多。專家利用人骨骨膠原中同位素分析後顯示,青海先民曾種植我們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時也攝取一定量的動物肉食,過著以粟、黍等為主食而漁獵為輔的生活。在喇家遺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麵條”,就是用粟,即小米麵製成的。
夏商時期,青海已經呈現出東西方不同文化型別共存發展的雛形。民和等多地發現的白種人的遺骨證明,中西交流早於張騫出使西域。
此時,小麥在河湟地區廣泛種植;醫療技術開始出現,河湟先民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開顱手術技術。而代表這一先進文化的人群,被稱為羌人。
羌族是西部的重要部族,距今約三四千年左右。當印歐人大量湧入新疆一帶時,幸虧有甘、青羌人,才有力地阻擋了印歐人的東遷和擴張。事實上,西方人將最早接觸到的東方人稱為China(羌)。
在安陽殷墟出土了很多刻有“羌”字的甲骨文。賈逵《周語》注說:“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覽》說:“神農氏姜姓。”《史記·六國年表》說:“禹生於西羌。”《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中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羌夷(人)也。”意思是共工、神農、大禹的身份是羌人。黃帝在位時,羌人曾助黃帝戰蚩尤。“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羌為周朝建政立下赫赫戰功。
周朝為了加強對全國各地的統治,分封許多功臣和貴族到各地做諸侯。齊、申、呂、許、秦等即是姜姓羌人受封建立的諸侯國。曾先後為周文王、周武王當過軍師的羌人傑出人物姜尚(子牙)即是齊國的開國君王。相傳周穆王曾駕著八駿之乘拜訪西王母。而西王母被認為是西部羌人的部落首領。
秦人或許不是最早進入中原的人,但他們是眾多進入中原的羌人中影響較大的一支。秦人自稱為秦或嬴,實為羌的轉音。顧頡剛指出,他們做了諸侯,做了貴族,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也許故意忌諱了,不再說自己是羌人而是說華夏人。至於留在原地的,當然還是羌,還是戎。
無弋爰劍,一個從秦國逃跑的奴隸,也是第一個記入中華史籍的青海羌人。我們現在還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真正的羌人。但至少說明無弋爰劍與羌人語言相通。《後漢書》中記載,他逃至黃河與湟水河之間,成為統一羌人的部落聯盟首領。
先秦時期,河湟應該屬於一個多元文化交匯、多種族交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不錯的地域,甚至是一段時期內,黃河上游文明高於中下游文明的地區,是早期華夏重要的文明補給區。那時,一種文化的向東傳播與擴張,都必然要經過青海這個現實的文化場進行折射和過濾。
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在總結羌人對中華民族的重大貢獻時指出,在中國文字中許多表示“好”或相當於這個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饈、善、義、羲等,都曾與羌人有關,這是對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華夏文化中西戎羌人文化的初源的遺存,這甚至意味著羌人確實創造了豐富的文明。
兩漢時期對河湟的開發——從歷史的中心到華夏文明的邊緣
在青藏高原半乾旱的牧區,每隔一定的年份都會發生災害,如雪災或旱災。而另一方面,青海東部耕地有限,已經不能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饑荒、戰亂,加上喇家遺址所反映出的洪水、地震,進入秦漢時期,青海文明由鼎盛開始走向衰落。
美國人賈雷德·戴蒙德在《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一書中,把一個社會崩潰的原因歸結為五點因素,即生態破壞、氣候變更、強鄰在側、友邦援助的減少以及社會自身缺乏應對之道。
黃河中下游經過夏商周時期的發展,由奴隸制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融合了羌等多種民族的華夏文明迅速崛起。
隨著漢朝大一統帝國的建立,中原政治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從商周時期已存在的華夷分野和農牧之別。
漢朝依仗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北逐匈奴,西擊羌戎。漢帝國的觸角第一次深入“扼束羌戎,藩蔽秦隴”的青海腹地。
公元前111年,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在青海設立第一個軍事據點——西平亭(今西寧市)。羌族不堪一擊,大量部眾不斷臣服於漢朝。
漢帝國陸續在青海東部設立了臨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樂都)、允吾(今民和)、允街(今甘肅省蘭州市紅古區)、河關(今貴德)等縣,並將青海東部地區正式納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縣體系中。漢朝派出護羌校尉,以加強對羌人的管理。東漢護羌校尉鄧訓經營河湟,深得民心。後羌民痛呼鄧訓早逝並建土樓神祠。
在漢代城堡中,規模較大、至今儲存完好的要屬王莽修建的西海郡(海晏縣三角城)。它是建於青海省腹地最早的一座郡級建置城。王莽設定西海郡,不僅將青海湖流域第一次納入中央王朝版圖,而且為青海湖流域賦予了政治、地理的文化意蘊,那就是歷代帝王追求的“四海一統”。
為加強對民族地區的控制,漢代創設了一種屯田實邊制度,進行了大規模移民屯田。由於大量關東貧民、秦雍世家在河湟安家立業,極大地充實了青海的人口,從漢武帝時起至東漢末,漢朝經營湟中300餘年,雖幾經戰亂而人口仍不斷繁衍增多,河湟漢族人口在這裡逐漸成為了多數。樂都老鴉峽出土的東漢“三老趙掾之碑”就追記了趙充國子孫,代代擁立漢室,屯田戍邊,立下赫赫戰功的事蹟。
面對華夏族的崛起,羌人很無奈,他們被同化、被驅逐,甚至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開始了長達千年的遷徙,上演了一部中國版的“出埃及記”。先零、燒當兩個部落中的大量羌人歸降內徙(稱東羌),而燒當、迷唐兩個部落的剩餘人員向西遠遁黃河源頭和青藏高原的腹地。在漢族無休止的擴張中,羌族逐漸離開了歷史的中心。
今天,分子人類學專家們透過基因圖譜找到了遠徙路線和分化的時間點。當時的羌人,有的向西,“出賜支河曲西數千裡,與眾羌遠絕,不復交通”,即後來成為藏族先民中的“發羌”“唐旄”;有的經過長途跋涉,抵達新疆天山南麓,後來成為文獻記載的“婼羌”的組成部分;有少數則北遷到今天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一帶。更多的羌人部落則沿著古老的“走廊”向西南遷徙,他們或是翻越秦嶺,或是穿過岷江河谷,或是穿過青藏高原東部的其他河谷,向西南大片尚未開發的處女地遷徙生存。
特別是沿著“走廊”向南方遷徙的羌人部落,由於各自到了不同的自然環境,有的到了河谷地帶,有的到了丘陵地區,有的則在深山密林中生息,加上其他種種因素的影響,決定了他們各自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或強大,或弱小;或農耕,或遊牧;或與漢族同化,或與土著融合,或與世隔絕,獨自生息,在此後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發展演變為今天的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族的各民族,如白、彝、哈尼、納西、傈僳、拉祜、基諾、普米、景頗、獨龍、阿昌、土家等民族。
外遷新土的羌人至少在兩晉南北朝以及唐宋時期還處在西部歷史的舞臺中心。譬如,李雄建立的成漢帝國;苻健、姚萇建立的前秦、後秦帝國;呂光建立的後涼王國。党項羌李元昊建立了“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的西夏王國。
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言:羌族是一個向外輸血的民族,許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羌族伴隨著中華文明的每一個腳印一步一步地從上古走來,它遠遠早於漢族和藏族,是中國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也是世界範圍內最古老的民族,是一個被歷史和人們忽視了的東方大族。
只是到了宋代以後,羌人在中原歷史舞臺上完全不見蹤跡。今天,我們審視腳下的大地,也僅在離湟水流域1000公里之外的岷江上游,於2000年前遷居於此的羌人,還保留著自己民族所獨有的生活習俗和族稱。
鮮卑族入主青海——一個英雄時代的大歷史
河湟從不缺少“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歷史話劇。鮮卑是繼匈奴之後又一個在北方崛起的強大民族。魏晉時代是中國民族關係劇烈變化的時期,鮮卑族從蒙古草原開始大規模遷徙到中國北方。
乙弗部在其首領的率領下,穿越祁連山,佔據了青海湖地區,與青海湖的原居民卑禾羌和睦相處。乙弗部就將牙帳設在了布哈河的中游,建立了一個蕞爾小國,史稱青海王國。
《北史》載:“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青海湖),周迥千餘里,眾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
其後,西遷而來的慕容部吐谷渾北渡黃河,漸次佔領了環湖地區,乙弗勿敵國解體,吐谷渾兼併氐羌,地方數千裡,號為強國。
吐谷渾國勢力範圍,東西長約1500公里,南北寬約500公里。公元540年,吐谷渾誇呂即位稱汗,定都青海湖南岸的伏俟城。吐谷渾效仿中原王朝推行封建政治制度,使青海中、西部眾多的羌人部落統一於其政權之下,改變了羌人部落互不統屬的狀況,並相互結合,形成了一個民族融合體,從氏族社會大跨步邁入封建社會,客觀上促進了青海湖環湖地區社會歷史的發展,推動了原始遊牧業經濟向商品畜牧業經濟的轉變。
吐谷渾人進入青海高原,不僅帶來了蒙古草原的畜種和生產方式,而且合理利用當地的地理環境發展畜牧業生產,尤其是創造性地利用青海湖環湖草場和湖中島嶼的自然地理環境,引進波斯種馬,改造鮮卑馬,培育出龍種馬,尤其是名馬“青海驄”,成為千古稱道的典範。
考古學家在青海德令哈巴音河南岸的郭裡木鄉吐蕃墓中意外地發現了一組吐谷渾人棺板畫。畫面展示了一位吐谷渾可汗與中亞、西亞的客人把酒言歡的場面,而在他們旁邊,一群商人正整理著駝隊,一峰滿載貨物的駱駝佔據了畫面中央。
就在吐谷渾抵達青海湖流域70年後,又一支拓跋部鮮卑西遷到青海東部,先後建都樂都、西寧,史稱南涼。南涼聯合戎人、羌人和漢人,在原有的牧業基礎上發展河湟地區的河谷農業。
只可惜南涼在與西秦的鬥爭中失利,南涼三兄弟中長兄禿髮烏孤酒後騎馬摔成重傷,不久後去世;次兄禿髮利鹿孤(即康王)設博士祭酒,開科取士,但在位3年就去世了;三弟禿髮傉檀窮兵黷武,他遷都樂都後,都城(今樂都大古城)被西秦乞伏熾磐所破,連他的太子武臺也做了俘虜。南涼王朝先後只存在了19個年頭就覆滅了。
英雄都已歸黃土,氣凌山嶽常崢嶸。
偏居一隅的吐谷渾立國長達350年,甚至在魏晉南北朝及隋末戰亂中難得地保持了祥和安寧,直到唐高宗龍朔三年(公元663年),被崛起的吐蕃所滅。
鮮卑族對青海的影響極其深遠。鮮卑語中的青海湖,音“屈海(青海)”,又因鮮卑所居,也被稱之為“鮮海(仙海)”。此後仙海與崑崙山、西王母神話傳說相聯絡,青海被賦予濃厚的神話人文意蘊,成為中國人膜拜的聖地。
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穿越千年時光的尋覓
相傳,3000多年前的一天,周穆王曾駕著八駿之乘拜訪西王母。兩人在瑤池(青海湖)相互唱和,並互致祝福。周穆王為什麼要萬里迢迢來青海?大概與夏朝後羿拜訪西王母的目的一樣,名為求取長生不老之藥,實為爭取西部部落集團政治軍事支援。
周穆王出訪時一定是帶領了龐大的“企業家”代表團,因為他帶去的絲綢品種就有很多,而且都很珍貴,有帛、貝帶、朱、錦、組、珠丹、朱丹等。從雙方宴會杯觥交錯、賦詩唱和的盛況來看,雙方達成了“合作協議”,可能還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周穆王見西王母,無疑開闢了最早的絲綢之路。
今天,考古人類學研究已經證明,在很久以前,就有一條古老民族遷徙的“羌戎走廊”的存在。早在幾萬年前,人們就已經沿著這個走廊進行著大規模流動。從秦漢時起,隨著地區性的行政建制的設立,這條古道上的民族交往日益頻繁,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火不斷,漢朝開闢的河西走廊被阻斷,而隨著吐谷渾的興起,溯湟水而上,翻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北兩岸西行的青海絲綢之路由於經貿繁榮而被人們所熟悉。
《北史》和《周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公元551年,吐谷渾的第18代國君向北齊國派遣了一支使團。西魏的軍隊探聽到這支隊伍迴歸的路線和時間,在涼州以西的赤泉襲擊了他們,俘獲了吐谷渾使團的將軍以及經商的胡人240人,駱駝、騾子600頭,雜彩絲絹數以萬計。吐谷渾一次就護送如此龐大的商隊,可見其在當時中西方商貿交流中的實力與地位。
柴達木盆地東緣和共和盆地曾經一度是兩漢以來絲綢之路青海道的重要驛站。上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曾發現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境內從夏日哈到巴隆之間200公里的狹長地帶就有200多座唐代吐蕃古墓,在這些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波斯金銀錢幣和絲綢織品,燦爛奪目的錦緞絲綢勾勒出青海絲綢之路曾經的繁榮和輝煌。都蘭豐厚的地下遺存,可以說是青海絲路曾經歲月的沉澱。
這條古道還連線了另一條通往江南的河南道,北起河湟,中經川西,南至成都平原。河南道既是吐谷渾政權統治時的官道,也是歷代青海河南及吐蕃等西域屬邦使臣和商人向中原朝貢萬物和物資交流的往來通道,還是佛教僧侶前往西域或天竺等地朝拜的重要路線。
7世紀初,吐蕃和大唐幾乎同時在亞洲東部崛起,他們開始承接絲綢之路已有的繁榮。信使、將軍、僧侶、商人、武士、遊俠、旅行家……形形色色的人像接力一般來來往往於古道中。
相傳,當年文成公主辭別父母遠嫁吐蕃,離開長安以後,跋山涉水,歷盡艱辛來到今天的日月山,由於離親人和家鄉越來越遠了,不由地思念起遠在長安的父母。她想起臨別時母親送給她一面寶鏡時說的話:若懷念親人時,可從寶鏡裡看到母親。於是文成公主急忙取出“日月寶鏡”,雙手捧著照起來,不照則已,一看反倒吃了一驚。原來文成公主從鏡子裡看到的並不是母親,而是自己滿臉憔悴的愁容。公主想到聯姻通好的重任,毅然將日月寶鏡甩下赤嶺。從此寶鏡變成了碧波盪漾的青海湖,而公主的淚水則匯成了滔滔的倒淌河。這條古道被後人稱為唐蕃古道。“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古道因文成公主而渲染上溫情脈脈的煙靄。
吐蕃傑出的贊普松贊干布統一了西藏高原,創造了文字,從漢地和泥婆羅引入了佛教。松贊干布在世時雖然還無法撼動大唐的強勢,但他所奠定的強盛基礎已為吐蕃後來的大擴張準備了條件。在文成公主入藏後,唐蕃實現了短暫的和平,但這並不能阻礙吐蕃擴張的腳步。吐蕃先後征服青藏高原上的蘇毗、白蘭、党項、吐谷渾,在唐蕃青海戰爭中也逐步佔據了優勢。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吐蕃勢力曾一度抵達渭河上游。
在吐蕃統治青海的100多年間,強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曾經生活在此的羌族、鮮卑族、漢族融入吐蕃民族,併成為吐蕃對唐軍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到現在,河湟流域的藏族還自稱是“嘉西番”。這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受漢文化影響;二是指漢人的後代。
吐蕃的佈防、大規模移民對宋代以後的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的藏族、土族聚居區的最終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