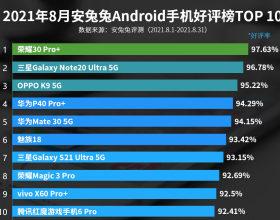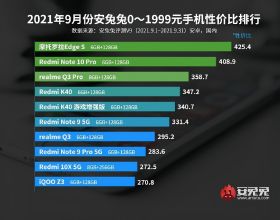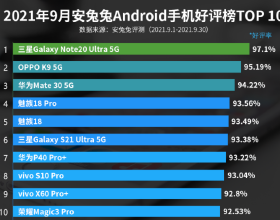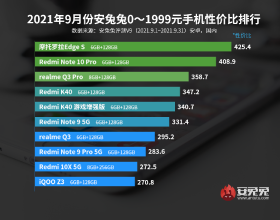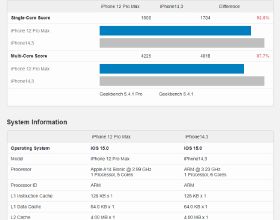大學生連記事12
1968年秋冬時節,駐雲貴川三省的54軍、13軍和14軍以及17軍的49師奉命換防。54軍接收第14軍在雲南大理地區的防務,第14軍則調往雲南開遠接收第13軍的營區。
54軍130師389團的周指導員一行,於1968年11月25日抵達孟定並接手學生連,14軍120團的劉指導員當即叫我們將原來他們部隊留下的肥豬殺翻,表示歡迎。11月28日,劉指導員、副連長、司務長一行在登車前特地趕來告別,彼此相處也不過就一個多月,連中多人竟與他們相擁而泣,三排女生大都哭成淚人一般,那場面是相當的感人。
說來這120團真夠意思,就在臨別前,劉指導員還再三提醒我們,一定要在旱季時將全年的燒柴備足,還說此前他們在小黑河深處已砍下兩堆,已經乾透,可先去運回以解燃眉之急。晚點名時,389團派來的連長拖著微跛的右腿,帶著副連長、副指導員、司務長和三個排長以及通訊員來到。在見面會上,他們都沒有發表什麼就職演說,只是在各位幹部逐一登臺亮相時,連長才介紹這是指導員、這是一排長、這是二排長、這是三排長……至於他們姓甚名誰、年方几何、哪裡人氏,連長隻字未提,以至於今天要為他們立傳時,連他們的大名都不知道。
這新來的連長有些另類,從第一次見面時對我們的稱呼便可略知一二。
以前,上級首長以及連隊幹部在給我們作報告或講話時,都將我們稱呼為“同學們”或“同志們”,我們對此都習以為常,以至於麻木不仁,而這新來的連長在第一次講話時,竟稱呼我們為“學員們”。
剛聽到“學員們”三字,我們就感到有些不對頭。
你別看這新連長的文字功底不怎麼樣,他對我們的這種稱呼一定是經過再三掂量的。
你想,他若將我們稱為“同志們”,豈不與他成了同一戰壕裡的戰友,有平起平坐之意不說,那還怎麼對我們進行再教育呢?若稱我們稱為“同學們”,多少就還有少許親近之感,這當然是他不願意的,何況眼下的“同學們”一個個都是老大不小,年齡分明與他的排長們一致了,都鬍子巴茬了,還“同學們”呢!
而“學員們”乃一中性詞語,部隊幹部到軍事院校進修,教官可以稱其為“學員”;蔣軍戰犯改造期間,也往往被稱呼為“學員”;今天他將我們稱呼為“學員們”,何錯之有!他的這種稱呼,真真叫人拍案叫絕、無可挑剔而有苦說不出來!他為這稱呼,一定在來之前就苦思冥想了許多時日。
他在“學員們”後,未及寒暄,便不鹹不淡地說,14軍老大哥部隊為我們砍好了兩堆柴,明天二排去把它弄回來,四點起床,早餐後就走。但是怎麼弄,帶什麼工具,連長也是語焉不詳。我們感到納悶的是,這路有多遠,犯得上4點就起床。
12月2日凌晨4點許,草草吃了早點,副指導員在前引路,連長拖著微跛的右腿斷後,我們一行便向小黑河深處開拔,時一天星斗還在西邊天空閃爍。
小黑河是耿馬縣與滄源縣的界河,兩岸高山懸崖,滿是密密的原始森林,不見曦月,盡皆漆黑一片。過了今之“小康橋”,就全是山間的羊腸小道,隱約間可聽得腳下河水嘩嘩的流淌聲,此情此景還真與《木蘭辭》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相似。
那日清晨,我們就在這深山密林中高一步低一步地摸黑走了約摸2個多小時,河谷內方見微明,正人困馬乏,昏昏欲睡時,突聽前面有人叫道:“國旗!”
果見一五星紅旗,飄揚於河對岸的峻嶺之上。說來也怪,這國旗竟比平時所見的更是鮮豔,更是奪目,更是莊嚴,更是神聖,更是令人肅然起敬、精神振奮,心潮澎湃了。
昨日打過前站當過先行的副指導員道:“那就是哨所。我們中午飯就在那裡吃。”
所謂哨所,不過就是兩三間茅草棚,俗稱“一片撒”,稍大那間是宿舍,床與我們的一樣,是四根木棒支起的竹片床,這茅草房雨季常漏雨,乾季就怕火,大風來時怕吹倒。
哨所的戰士,大概也就是一個班的樣子,是時他們正圍坐在茅草棚前火邊搞“天天讀”。
雲南邊境哨所(資料圖)
孟定境內的國境線長達47餘公里,在大山深處的邊境線上,類似的哨所不知還有多少。據說有的哨所就只有那麼二三人,一月之中能與連長相見的次數都很有限,有人幾年兵當下來,還說不清團長是什麼模樣。在這終年與世隔絕的寂寞之鄉,你咬著牙或許可以呆上三月半年,倘若要你也像邊防兵一樣也長年累月地呆下去,你受得了,在得住嗎?
過了哨所,越往裡走,兩岸高山越發逼窄,而原本就自高向低流著的小黑河,就有了奔騰之勢,大概又往前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了劉指導員所在連隊的砍柴處,那裡有小山似的兩堆乾柴。連長叫我們將柴扔於河內,讓它順流而下。
理論上講,乾柴浮於自高向低流動著的河面之上,自然會順水而去,確實能節省許多的勞力,而且我們剛投下的柴,還真的被湍急的河水帶走,霎時沒了蹤影。當時還擔心著這水流太快,若將柴投完再趕至駐地下壩,或許會有許多柴已經流走,便建議連長派出一人趕回連裡,要他們立馬派人到河岸恭候。待將全部乾柴投完已是12點過了,眼見已是大功告成,肚子也很有了幾分餓意,都忙著沿河而行欲趕至哨所吃飯。
哪知剛轉過一彎,不禁令人大驚失色,只見方才投下的乾柴紋絲未動,盡皆齊齊整整地停於河面之上。原來這柴全被倒於河內的樹幹擋住,而那樹幹又被河裡的礁石卡了個結實,這真成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景象。
在滇池邊長大的楊安雖是高度近視,卻是一遊水好手,他與家驊兄等立馬將衣服脫了,下至河內。我亦耐不住寂寞,見河面平靜如許,自恃水性也還勉強,亦跟著游去,欲與他們一起將卡在岩石縫中的樹幹拖出,哪知遊至礁石旁剛拉住樹幹,正欲站起,水面之下卻是股股暗流滾動,兩腳當即被這漩渦裹著拽著,直往水底沉去,據說岸邊的人還來不及喊叫,霎時便不見了我的頭影。所幸我的手還緊緊抱住樹幹,而且這樹幹是被礁石卡住,正騎在礁石上撥弄樹幹的副指導員見狀,一把死死抓住我的手臂,方把我拖出水面。
眾人見狀倒吸了一口冷氣,一時不敢再貿然行事,大約用了半個多小時,才將卡在礁石間的樹幹拽出,那些浮於江面上的柴塊早等得不耐煩,見有了一點空隙,便急不可待地、爭先恐後地,挨挨擠擠地、浩浩蕩蕩地向下漂去。
這山間河流中,奇形怪狀的礁石所見皆是,而倒於河面上的樹幹也不是一株兩株,柴被擋住的地方,當然也就不是一處兩處。下水放柴,人人有責。先前還只是站在岸上乾著急的旱鴨子們沒了耐性,也把那衣褲去了,在水不太深的河段拖著樹幹。
怎奈河底也是凸凹不平,深淺不一的,只見戴著一千多度近視眼鏡的楊安不留神,一腳踩空當即跌入水中,待慌忙爬起,怎麼眼前竟是一片朦朧,總覺得是哪裡不對,思之再三,恍然大悟,原來是眼鏡沒了,於是捶胸頓足道:“眼鏡,眼鏡,我的眼鏡!”
眼鏡掉於河中,與大海撈針無異,任你千般喊叫,萬般呼喚皆屬徒勞,所以當後來家驊等幾位“眼鏡”的眼鏡也掉於河內時,就心平氣和多了,既然千呼萬喚都是白搭,索性不去管它,一任它隨水漂至薩爾溫江。
時值冬季,北半球各地晝短夜長,這深山密林的河道內,太陽更是落得早,才是下午四時就沒了陽光,氣溫驟然下降,泡在水中就很有幾分寒意,而腹內也有十多個小時沒有進食了,都已是前胸貼著後背,飢腸轆轆的了。此時此刻,方把那飢寒交迫四字型會得真真切切。
副指導員見這事不是一時半會就能完成得了的,有如就這樣耗著打疲勞戰,不如先到哨所吃了飯再說。那連長卻是鐵青著臉,一氣不吭,彷彿別人向他借了白米還他粗糠一般,副指導員自感沒趣,便不再吭聲。我們在一旁看得清楚,覺得這連長太過不近情理,但看著這位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負傷至腿微跛的老兵,始終在河中忙碌的身影,還是叫人油然而生敬意的。
直至黃昏時分方才到得哨所,一個個早餓得心慌心跳,哨所戰士立馬將飯端出,四戰士抬出兩大行軍鍋魚肉,大家早已餓極,心裡雖然非常感激,卻都來不及說聲謝謝,一個個急吼吼地操起碗筷,便狼吞虎嚥起來,開始幾碗竟無人來得及吐骨,皆連著魚刺嚼嚥了下去。
那魚是異常的環保鮮美,連湯帶肉並飯,每人吃了不下三四斤,把哨所戰士驚得目瞪口呆。但是,麻雀吃蠶豆,忘了與屁股商量。當時只圖盡情吃喝,夜裡卻是腹脹難熬,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了,有人還就此落下了胃病。
待吃飽喝足,一哨所戰士掏出一包藍殼“金沙江”香菸(當時每包價0.29元,戰士每月津貼6元)見人就發,“喜歡也要抽,不喜歡也要抽,管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抽”。盛情難卻,卻之不恭,我那時還談不上煙癮,也點燃起來,霎時這嘴裡竟有一股幽幽的既香且甜之味,於是眯縫著眼睛,看著縷縷白煙在頭上繚繞,愜意非常。
人於飢寒交迫後,能吃上一頓飽飯原本該感恩再三了,飯後還能咂上一支菸,那就與封侯無異了!從此,方知煙鬼們津津樂道的“飯後一支菸,賽過活神仙”,並非全是他們抽菸的藉口,實乃肺腑之言,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以後,這煙也成了我每天的不可或缺之物,遺憾的是,儘管在幾十年中已經抽菸無數,從8分錢一包的“等外菸”、“經濟牌”、“春耕牌”到百元以上一包的極品煙,林林總總悉數抽過,卻沒有再抽出過似那日那一股幽幽的既香且甜,醇厚迷人之味。四五十多年過去,活到了這般年紀,吃過、抽過、見過的已是不少,套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再也沒有吃到過那日似的好魚和抽過那日似的好煙了。
副指導員為人實在,是個知道感恩的人,他說,這魚是公安團哨所的排長,領著戰士不顧違反紀律的風險,用手榴彈去河裡炸來的。始,副指導員還很是認真地推辭了一番,見那排長和戰士執意不聽,再說未免見外,便來了個客隨主便。副指導員動情地說“人家把一個月的油都用完用盡了!老大哥就是老大哥,待人太實在了!”
此前,我們也有過外出幹活時,就便在附近連隊食堂搭夥用餐的事,至於怎樣了結,那是司務員和一波同志的事。今天大家都覺得不能不有所表示了,若報之以錢財,加倍奉還,簡直就是對戰士們一片真情的褻瀆,但不聊表心意,抹抹嘴角,腆著肚皮,拍拍屁股就走那還叫什麼人?看著天色向晚,情急之中,有人道“何不贈送像章?”眾皆道好。
我們把師部剛發下的鑄有小米加步槍的像章從胸前取下,列隊站定,舉行了向哨所舉行贈像章儀式。沒想到戰士們竟是欣喜異常,那排長道:“我們的戰士最喜歡的就是主席像章。”
記得還在昆明時,那14軍的參謀曾說過,他們團有兩件事聞名全國,其一是歌曲《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就是他們團的戰士在孟定寫的。當時心下還半信半疑,今見邊防戰士對一主席像章竟珍愛若許。戍邊多年的14軍戰士,與邊防團同沐於一陽光之下,在水分、土壤都完全相同的環境裡,自是表達不盡的愛戴之情,是時有戰士情發乎其內,譜寫了那麼一曲歌曲,正是自己內心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本是順理成章,瓜熟蒂落的事。其實,在那種特定的環境裡,漫說是隻寫了那麼一首,就是寫出了十首八首,也沒有什麼可值得驚詫的,都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事。
年華似水,五十多年過去,經歷過的許多事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日漸模糊,在新陳代謝中一一逝去,但當年在那高高的阿佤山上,在那密密的原始森林中,在那清清的小黑河畔的邊防哨所吃過的那餐飯,卻始終揮之不去,甚至在對比中越發地清晰了。
【深耕戰爭史,弘揚正能量,歡迎投稿,私信必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