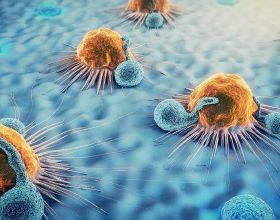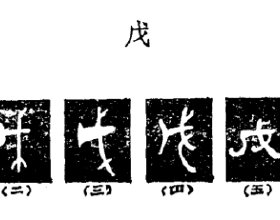2017年2月的一天,阿什瓦德·可汗(Aswad Khan)早上醒來,發現手機裡有老同學發的慶祝簡訊。
“你最好的朋友結婚啦!”簡訊裡寫道,“你一定會去參加婚禮吧?恭喜啊!”
阿什瓦德愣住了,一股涼意湧上來。
最好的朋友艾哈邁徳(化名)要結婚了?
他們是從小玩到大的朋友,最鐵最鐵的兄弟,但是,他從來沒聽說過他結婚的訊息。
阿什瓦德開啟臉書去看艾哈邁徳的頁面,卻發現對方已經取關了他,也限制他訪問自己的個人資料。
這不是臉書出問題,在Instagram上也一樣,最好的朋友把他遮蔽了。
在朋友的評論區,到處是其他朋友們傳送祝福,還有人問阿什瓦德會不會參加婚禮。
那年阿什瓦德31歲,他躺回床上,靜靜地哭起來。
好友的絕交是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過去5年,他不斷經歷熟人與他斷絕來往,
他發的簡訊和電話總是沒人回,還有朋友的家人警告他們,不要與阿什瓦德交往。
阿什瓦德像是身處一個虛擬的監牢,周圍人像是躲避瘟疫一樣,悄悄躲著他。
背後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做錯了什麼事,而是因為——
他拒絕當FBI的線人。
阿什瓦德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富裕家庭長大,從小,他經常去美國旅行,他在康涅狄格州有親戚,每年夏天都會去看望他們。
高中畢業後,他選擇到波士頓的東北大學讀商業管理,在那裡度過五年美好時光,交了很多朋友,還成為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死忠粉絲。
2011年,阿什瓦德成為“海歸”,回到巴基斯坦工作,但他仍然想看望親戚,於是申請了一個持續6個月的訪問簽證。
他住在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顛市的姑媽家,最初的幾個月,和以往的美國生活一樣,很平靜,很正常。
但2012年2月9日,一切全變了。
那天上午,阿什瓦德從睡夢中醒來,聽到樓下傳來敲門聲。
那會兒,他的姑媽、姑父和表兄弟們都出門了,他的手機響起來,顯示的是表弟的號碼。
阿什瓦德以為是表弟他們忘帶東西,拿起電話說,要不要給他們開門。
“我不是你的表弟。”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從電話那頭響起,“我是聯邦調查局(FBI),就在你家門口。”
阿什瓦德的心狂跳起來,他不知道為什麼FBI會來,而且為什麼要冒用表弟的號碼。
他按照指示給他們開了門,門口站著兩個西裝革履的男人,一個來自FBI,一個來自康涅狄格州警察局。
阿什瓦德和他的律師後來確認,這兩人的分別是聯邦特工安德魯·克羅普弗(Andrew Klopfer)和警探安德魯·伯克(Andrew Burke)。
兩個安德魯告訴他,他們要帶他去鎮上的一家小餐館,邊吃邊聊。
一上車,安德魯就說阿什瓦德看上去很高,和資料裡顯示得不一樣。
“過去一週,我們派人一直監視你,開車尾隨你。你注意到了嗎?”
阿什瓦德搖搖頭,感到更加恐懼。
在餐館裡,兩人盤問阿什瓦德在巴基斯坦做什麼,為什麼來美國,家庭狀況如何。
聊了20分鐘後,FBI的克羅普弗談到重點:
他們希望阿什瓦德為他們工作。
“我們希望你能為我們工作,提供美國和巴基斯坦的情報。簡單地說,我們希望你能在美國和巴基斯坦的清真寺當線人和間諜。”
那時,阿什瓦德不知道“線人”是什麼意思,對面兩人告訴他這意味著站在好人那一邊,也就是他們那邊。
克羅普弗告訴他,這麼做是為了抵抗巴美兩國的恐怖主義。他們已經查過他的身份,知道他很清白,可以被信任,所以把機會交給他。
可是……當線人和間諜?
阿什瓦德從沒想過自己的職業選擇有這些。
他直接拒絕了,不是因為別的,只是他們家還算有錢,不需要當線人賺錢,
而且他的性格也不適合做這種工作。
安德魯們試著說服他,只要他肯接受這份工作,FBI可以提供美國公民身份和各種福利。
他們還能讓他成為一個有權勢的人,一個“不會被欺負的人”。
簡單地講,只要當FBI的線人,FBI就能罩著他。
三人談了兩個小時,阿什瓦德全程坐立不安,他說他很少去清真寺,也不想監視任何人。
最後,看無法說服他,安德魯們只好放他回家。
臨走前,FBI的克羅普弗說,這場談話不要告訴任何人,尤其是律師。
這句話他不是說著玩的,但當時的阿什瓦德太不安了,他回到家後馬上給姑媽打電話,說了整件事。
姑媽覺得事情很奇怪,很快聯絡上一名律師,律師打電話給FBI和康涅狄格州警局,警告他們,以後不能在沒通知律師的情況下直接聯絡阿什瓦德。
幾通電話,把FBI的雷點全踩中了。
一週後,克羅普弗告訴律師,說他們要在聯邦檢察官面前和阿什瓦德聊聊。
律師同意了。
這次見面非常正式,一進入會議廳,阿什瓦德就發現FBI特工們表現得非常冷漠,克羅普弗更是一臉怒色。
FBI的問題和餐館裡的基本一樣,問他的生活和政治傾向,接著,問題漸漸變得奇怪起來,開始問阿什瓦德是否認識特定的恐怖組織,對幾起恐怖襲擊是否瞭解。
這番問話,像是把阿什瓦德當恐怖分子對待。
阿什瓦德怒氣衝衝地說,他來美國是接受教育的,他是守法公民,“我不想招惹你們,但似乎我的有色人種、巴基斯坦人和穆斯林這三重身份,導致我此刻站在這裡。”
檢察官安撫他,這和種族主義無關。
在阿什瓦德說他要去醫院看望生病的姑父後,他們就放他走了。
媒體後來查到,關於餐館和會議上的所有檔案,都掩蓋掉了“提供線人工作”和“談及恐怖主義”的資訊。
回去後,阿什瓦德以為一切結束了,他在美國呆到簽證期結束的最後一天(以此證明他不心虛),在肯尼迪國際機場啟程回國。
有生以來,他第一次在登機牌上看到SSSS的標誌,這是“二級安全檢查選擇”的縮寫,意味著他比普通乘客多進行了一些檢查。
他以為僅此而已,但誰知道,這次離開美國後他再也回不來,他的朋友們也遭殃了。
2012年5月,也就是阿什瓦德回國後的一個月,他的童年好友費薩爾·蒙希(Faisal Munshi)要去美國開會。
蒙希擁有巴基斯坦和加拿大雙重國籍,是一家大型食品供應公司的老闆,也是一家跨國披薩連鎖店的巴基斯坦經營權持有者。
作為老闆,每兩年他要去拉斯維加斯參加全球會議,他之前已經去了很多次,但那一次,他被海關攔住了。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特工問了他好幾個小時,全是關於阿什瓦德的問題。
他們說蒙希在幾年前給阿什瓦德買了張去多倫多的機票,問他為什麼。
蒙希說兩人是朋友,每年都會聚一聚,他買票是讓阿什瓦德去多倫多看他。
這事很簡單,但特工們認為很不簡單,他們拒絕讓蒙希入境美國。
一年後,蒙希要去美國參加另一場公司會議,這次是從迪拜起飛。
但他仍然失敗了,迪拜機場的官員告訴蒙希,他沒被獲准飛行。
蒙希不安起來,他的妻子是美國人,兩人經常要去美國,一直被限制入境該怎麼辦。
在律師的建議下,他打算開車跨越邊境。
2014年,為了參加親戚的大學畢業典禮,他開車前往水牛城的一個過境點,但他再次被攔住,而且遭到的待遇更差。
“開車去水牛城被拘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經歷。”蒙希告訴媒體,“他們把我當成罪犯,關了我6個小時,把我拖到不同房間,不讓父母見我。我見了一個又一個移民官,問他們為什麼,他們都說無可奉告。”
最後,蒙希拿到批薩連鎖店美國總部的信,希望證明他是好人,但這沒什麼用,他還是被禁止入美。
為什麼美國突然不再歡迎他這樣的大老闆呢?
蒙希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在幾年前給阿什瓦德買了機票。
類似的遭遇,還有很多。
有十幾個朋友告訴阿什瓦德,他們在美國機場遇到麻煩,海關盤問了他們幾個小時,全是關於阿什瓦德的問題。
有海關官員直白地說,讓他們不要和阿什瓦德來往,阿什瓦德是危險分子。
為了安全入境,一些朋友打電話和他道歉,說只能把他的聯絡方式刪了,在社交平臺上取關他,這樣才能證明他們不是朋友。
更多熟人沒有通知他,悄悄斷掉了和他的一切聯絡。
阿什瓦德和律師相信,他是上了美國的潛在恐怖分子名單,這是FBI給他的報復。
前FBI特工邁克爾·格曼(Michael German)說,這種形式的“報復”很常見。
在911以後,FBI的一大工作是招募線人,他們和美國海關合作,找到那些來自重點國家的人,或者是移民,對他們進行監視和審查。
審查通過後,FBI會丟擲橄欖枝,讓他們當線人,報告發生在自己社群裡的可疑動向。
這種工作對FBI來說很重要,如果有人不願意幹,就會被報復打擊。
“這些年來,很多人指責FBI在他們拒絕當線人後,把他們列入禁飛名單。
特工需要線人,這是他們釣大魚的手段,所以當人們拒絕時,他們會懷恨在心。”格曼說。
“他們的態度是,‘我們給了你機會,讓你站在我們這邊。但你拒絕了,這就意味著你站在我們的對立面。’ ”
阿什瓦德的律師納茲·艾哈邁徳(Naz Ahmad)說,他認為阿什瓦德大機率在禁飛名單和恐怖分子監視名單上,但FBI拒絕透露名單上有沒有他。
因為他不是美國公民,他沒有基本的維權手段,所以也無法檢視名單。
隨著越來越多的朋友遇到麻煩,在巴基斯坦,關於“阿什瓦德是恐怖分子”的謠言也出現了。
事情發展到最後,很多人甚至不願意見阿什瓦德,他們認為美國政府針對他肯定是有道理的,紛紛在臉書上把他刪除。
於是,阿什瓦德進入文章開頭的狀態,電話和簡訊沒人接收,婚禮和派對沒人邀請。
他基本“社會性死亡”了,
用他自己的話說,雖然FBI沒抓他,但他已經處於一個“無形的監獄”。
2018年,阿什瓦德想知道如何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刪除。他給美國國土安全域性提交檔案,但安全域性說他們“既不能確定也不能否定他是否在聯邦監視名單裡”。
前特工格曼說,一旦上了名單後,很難刪掉名字。
“人們的名字上了名單後,基本會一直留在那裡,因為FBI覺得沒必要把他們刪除。毋寧說,他們覺得把名字保留更好,因為,說不定未來這些人就會犯事呢?”
“把某個人列入監視名單,然後忘記這事也是很常見的。至於它會對那個人產生多大的影響,FBI不關心。”
到現在,快10年了,阿什瓦德的朋友們仍然受到影響,阿什瓦德自己也不敢出國旅行。
他擔心美國政府可能給其他國家散佈謠言,自己如果去別國旅行,也會面臨關押和審問。
這種動彈不得的感覺,讓他患上抑鬱症和偏執症。
美國的線人數量有15000人,在監視名單上的人有120萬人,像阿什瓦德這樣的倒黴人不少見。
律師納茲·艾哈邁徳說,FBI的做法造成嚴重的聲譽損害,這種損害雖然不可量化,但是真實存在。
“他的名譽和友情受到毀滅性打擊。失去朋友,沒有參加最好朋友的婚禮,這些都是傷害。”
不久前,阿什瓦德在卡拉奇市遇到曾經最好的朋友,那個沒有邀請他參加婚禮的人。
他們已經兩年多沒說話了,也沒見過面。
這次一見面,朋友崩潰地哭起來,說他不是討厭阿什瓦德,只是太害怕。
他也是為了保護婚禮上其他客人,不讓他們受影響。
“我很受傷,但沒關係,我懂。”阿什瓦德說。
“但歸根結底,還是你相信了FBI的話。你害怕,是因為你相信我真的是恐怖分子。”
朋友聽聞此言,不做聲了。
阿什瓦德不知道,相信他是恐怖分子的人有多少,
又要過多久,他才能洗清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