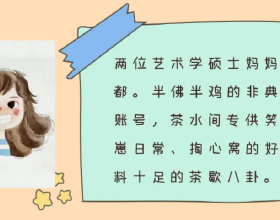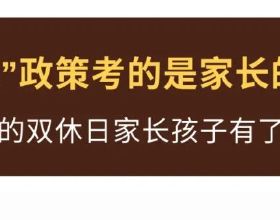“當我穿過一片農田,一段回憶湧上我的心頭。那是一個晴朗涼爽的秋日午後,當時我和十幾個朋友坐在陰涼的後院,舉杯敬酒,講述最近的生活。我怎麼也想不到,那會成為我餘生痛苦的根源。”
說這段話的人,名叫斯賓塞 L.施耐德(Spencer L. Schneider),是美國紐約的一名律師兼海洋救生員。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深陷極端精神團體23年的受害者。
據外媒報道,這一切都始於1989年春天。那時,斯賓塞29歲,每週60小時的高強度工作讓他毫無喘息的時間。父親在不久前離世,他的很多朋友也在婚後搬到了郊區,斯賓塞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就在那時,他認識了馬爾科姆,一名常春藤高校的研究生。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他們逐漸熟悉。後來,馬爾科姆向他透露,自己還是一所神秘“學校”的學員,該“學校”正在邀請精英人士加入其中。
但斯賓塞覺得,馬爾科姆口中的這所神秘“學校”聽起來很奇怪,像是一種邪教。不過馬爾科姆還是不斷告訴他,這是一個公認的、不同尋常的學習團體,它擁有偉大的導師及有趣的想法。
馬爾科姆說,這所神秘“學校”來去自由,第一個月是免費參加的,後續的學費也僅為每個月300美元(約合人民幣1900元)。
架不住馬爾科姆的勸說,斯賓塞答應加入了。
一週後,他們來到富蘭克林街拐角處的一座舊工業大樓。馬爾科姆帶著斯賓塞進入一個搖搖晃晃的小電梯,它通向一棟老舊但整潔的閣樓。
在那裡,大約40名二三十歲模樣、穿著整潔的男男女女靜靜坐在四排椅子上。當斯賓塞坐下時,幾個人抬起頭,友好地對他微笑,斯賓塞的疑慮開始被這種熱情所打消。這時,這所神秘“學校”的負責人——莎朗·甘斯出現了。
她沒有透露任何關於自己的資訊,甚至沒有透露她的姓氏,沒有人認出她。但其實,莎朗·甘斯曾參演1972年的科幻片《第五號屠宰場》,她看上去聰明、自信、充滿活力。
斯賓塞成為了這裡的一員。據報道,在高峰期,這個“學校”一度擁有數百名學員,他們沒有任何迷信活動,沒有武器,沒有世界末日的預言,也不相信外星人會來拯救人類。他們似乎沒有做任何會被認為是邪教的事,甚至沒有留下自己的真名。
莎朗·甘斯告訴他們,如何透過努力實現自我意識的提升,這將改變每個人的生活。
他們不需要在地鐵裡分發傳單,也不需要挨家挨戶敲門傳教。恰恰相反,學員們需要發誓,對“學校”的一切保密。
那麼,這樣一個看似無害、提升自我價值的團體,最後又是如何變成斯賓塞口中的邪教的呢?
大約上了一個星期的課程後,斯賓塞接到一個自稱大衛的人的電話。大衛說,他將成為斯賓塞的“支持者”。在這所神秘“學校”,每個學員都會被分配一個“支持者”,“支持者”會在課餘時間與該學員交談。
在此後的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裡,大衛每天都會給斯賓塞打電話。從來沒有人對斯賓塞如此關心過,斯賓塞變得非常信任大衛,並向他透露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
但斯賓塞不知道的是,大衛與此同時也正在向莎朗·甘斯報告他們交流的每一個字。
一週年之後,斯賓塞變成了老學員,他花在老朋友和家人身上的時間減少了。他開始認為,他們都沒有“學校”的朋友重要。
而“學校”的一切,也開始變了。
莎朗開始深入干預他們的個人生活,迫使他們做一些瘋狂的事。比如,當已經有了孩子的已婚婦女懷孕時,莎朗會讓她們流產,或把孩子交給“學校”裡其他無法懷孕的夫婦撫養。斯賓塞說,在莎朗的催促下,這樣的事情至少發生過兩次。
莎朗還給學員們安排結婚伴侶,強迫夫妻離婚。她在“學校”中培養了學員們對她的信任之後,又進一步試探著學員們的底線,想讓他們完全為己所用。
斯賓塞說,莎朗缺乏同理心,金錢和權力才是她最感興趣的東西,“學校”對她來說就是一門生意。
多年來,學員們一直被灌輸,提升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為了“學校”利益從事艱苦的無償勞動。比如,只有足夠優秀的人才能被莎朗選中,幫助她從事建築工作:凌晨2點30分站在梯子上,手裡拿著油漆滾筒,瘋狂地粉刷天花板。還有人被選中,享有為莎朗做所有飯菜的“特權”。斯賓塞則“幸運”的擔任過司機。
但莎朗最喜歡的消遣,還是羞辱學員,尤其是女性。莎朗會在眾人面前用最骯髒的語言辱罵她,獲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莎朗還說服了她的一些富有學員為她購買了價值8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000萬元)的公寓。
2021年9月24日,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兩名女性把這個極端精神團體和主要負責人告上了法庭,她們表示,莎朗向學員撒謊,說為自己服務是一種榮譽、特權和自我提升的象徵。
該訴訟還提出,莎朗的組織“被指控進行系統的身心虐待、虐待兒童、性虐待、私人收養、包辦婚姻和金融犯罪。”
許多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的前學員表示,他們在離開“學校”後經歷了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就好像這個世界向你敞開了大門,然後突然被關上了。”29年前逃離的56歲女演員貝茜·溫斯洛(Betsy Winslow)回憶道。
另一位19歲的學員坦承加入的原因。“因為我們很孤獨,我想我們都真的很孤獨。”
而斯賓塞則將莎朗這種虐待比作美國邪教“NXIVM”給其女性成員身上打上烙印的儀式。“也許我的身體上沒有像她們那樣的烙印,但我的大腦、我的記憶都印有莎朗的痕跡。我還沒有把這段經歷拋到腦後,甚至可能永遠都不會。這是我人生中的23年,如同一場噩夢。”
美國邪教研究專家瑞克·羅斯在接受採訪時則說:“我在這個領域工作了30年,這是我遇到過的最隱秘的精神團體之一。”
然而,帶給斯賓塞這種痛苦的莎朗早已年邁,已經於2021年1月22日在自己價值800萬美金的豪宅中死去了。
而前學員們發起的集體訴訟,還在艱難地進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