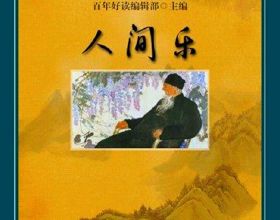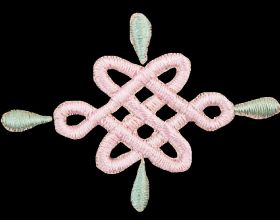【文化評析·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③】
作者:孟繁華(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西風東漸”開拓了我們的文藝視野,深化了我們對文藝的認識。隨著中國文藝的不斷髮展,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一味地追隨西方文藝和批評的話語體系,中國文藝就不可能建立起自身的主體性。而且,這些建構於西方文藝創作基礎上的文藝批評和理論,面對日益豐富和發展的中國現實,越來越失去批評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於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新認識本土文化資源,成為當下非常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潮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和感知了歐美文化的性質和價值觀,對世界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有了新的認知,因此也進一步加深了對本土文化傳統的認識和了解。這時,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本土文化資源的重要性,是一種對他人、對自己都瞭然於心的文化自覺。在此情況下,我們才能更加明確中華本土文化傳統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近年來中國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證實了這一點,廣大作家紛紛向本土文化汲取資源,創作了大量豐富、生動的作品,不僅深刻揭示了傳統文化資源經過現代闡釋仍然可以有效傳承,同時也表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和相互融匯,使中國文化無可避免地具有可以通約的世界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具有重要意義。
一直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是一個極其活躍和富有活力的領域,比如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等,羅宗強的《明代文學思想史》、陳伯海的《中國詩學之現代觀》、汪湧豪的《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及體系》、蔣寅的《清代詩學史》、周裕鍇的《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十講》、鄔國平的《中國文學批評自由釋義傳統研究》、張健的《知識與抒情》、宋燁的《詩與識:中國古典詩歌審美統一論》、廖可斌的《明代文學思潮史》、呂雙偉的《清代駢文理論研究》、張伯偉的《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吳承學的《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慈波的《文話流變研究》、彭玉平的《況周頤與晚清民國詞學》、蔡德龍的《清代文話敘錄》、譚新紅的《清詞話考述》等。但是,由於學科壁壘,除了古代文論專業的學者外,文學理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學科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古代文論研究領域發生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古代文論的學者並不是故步自封,不是“在故紙堆裡討生活”,當然從事的更不是“博物館的學問”。他們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再闡釋,隱含著世界性和開放性。也就是說,當下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有著世界的眼光和今天的視野。這個“古代文論”,同時也是“現代”的,因此無可避免也是“當代”的。
中國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與意義,一直是當代文藝批評家和研究者普遍關心和焦慮的問題之一,文藝批評和研究的理論支撐與依據從哪裡獲得,也是近些年來當代文藝研究探尋之所在。這時,很多朋友希望回過頭來,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文藝中尋找本土資源,透過對本土資源整體的提煉,進行“現代闡釋”,然後應用於當代文藝批評和研究。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實現文藝理論突圍,在吸納世界優秀文藝理論的同時,更關注本土的文藝理論傳統。透過文藝各個領域的共同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文藝經驗和實踐的批評話語體系,在解決我們文藝理論困擾的同時,也能夠同西方文藝批評構成真正的對話關係。包括中國古代文論在內的中國學術史,某種意義上就是對中國學術元話語不斷詮釋的歷史,或者是中國學術元話語的闡述史。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克羅齊意義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也是敘事的一種。歷史只有在當代發生迴響,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這個迴響,就是當代人對歷史進行的新詮釋。古代文論同理,我們如果有能力對其進行“現代”的詮釋,那麼它應用於當代中國文藝批評的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另一方面,面對豐富駁雜的傳統文化,要弘揚的究竟是什麼?就這個問題,費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覺”說提出了一條思路。他認為,所謂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並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建立,不帶任何“文化迴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其實就是一個追求文化自覺的過程。這個過程艱鉅複雜、充滿挑戰,只有在充分認識自己的文化和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相互貫通,最終實現和平共處、各取所長、攜手發展。對於中國新文藝來說,從誕生的那天起,它的本土性與世界性就是並存的。今天,在這個基礎上的繼承和創新就是現實的、充滿可能性的。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