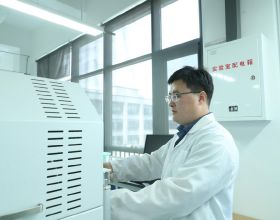中國藝術品和歐洲藝術品:反映和歪曲

在歐洲人對圓明園的描述中,第一部最有影響的,是一名法國耶穌會士的使者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所寫的一封著名書信。他於1738年來到中國,直到他1768年去世都是作為一名宮廷畫家為乾隆皇帝服務。
他的這封信寫於1743年,在這座花園完工的前夕,寄給他的故鄉多爾的阿索先生。這封長信於1749年以書信集的形式在法國出版。之後,它被翻譯成英文。1752年,它至少在三本英國雜誌上發表。王致誠是以歐洲人的眼光最廣泛描述中國的現實花園的人,他保留了中國帝王的主要花園宮殿建築群的下一個50年的最詳細的描述。
因此,在使歐洲人瞭解中國的宮廷文化和中國宮廷文化強烈地影響英國自由流動的花園景觀的發展方面,王致誠的書信被證明是重要的。這被法國的中英式花園所複製。結果,這完全是中國的花卉藝術品。最重要的是:在現在的背景之下,這封信揭示了審美過程的翻譯。為了使中國的異邦藝術在歐洲被理解、被使用,這是所必須的。

王致誠告訴我們:他和其他的耶穌會傳教士,包括著名的郎士寧,居住在一個緊靠圓明園的教堂建築群裡。他們每天在宮廷工作。乾隆每年有10個月居住在圓明園,在這一時段,他們大部分時間畫中國風格的作品。王致誠也提到:作為一個宮廷畫師,他每天見到皇帝,享受整座宮殿,包括帝王的居處。因此,他的信表面上是外國人,但實際上是一個精英帝國文化創造者的內部觀察者的獨特視角。
他在皇帝最核心的圈子中,與皇帝如同滿洲官員那樣親密。他共享、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乾隆的文化經驗。更進一步地說,不像隨之描寫圓明園的外交家、軍人或旅行者,王致誠明顯地受一個使者對跨文化交流的慾望的激勵,即使這種慾望反過來被他激勵。正如他所承認的:更感興趣的目標是促使中國包容基督教。事實上,王致誠和他的同事是持續地把中國的所見所聞傳回到歐洲的核心選手。那時,中國經常被視為一個潛在的進步社會、道德和政治觀念的來源。

王致誠把圓明園的眾多風格意識形態的假設、審美反映、敘述策略這些被後來的來自歐洲的旅行家和評論家重申的因素,從許多細緻的描述和註解中顯現出來。因此,這些組成了在理解中國的建築和花園方面一個佔統治地位的典範。最驚訝的是:他公開宣稱圓明園這座宮殿建築群最終的不可理解性。
一個原因是它規模巨大。單是與多爾的居住區域的規模比較,他在聲稱不可能做一個計劃之前,引用了超過200座宮殿和許多供太監居住的房子,因為他說“為做那計劃,我將不得不至少花3年的時間,其它什麼事都別幹”。另一個突出的特徵是:無盡的多樣性的土地,包括樓房的樣貌、橋樑的造型、沿湖岸的植物和建築、燈籠的材料和種類、窗戶和門的形狀、走廊和畫廊的輪廓。
總結起來,王致誠對他們的(中國人的)富於創造力的精神感到驚訝。他陳述道:這令人欽佩的多樣性不僅在整個樓房和景色的象徵性方面存在,也在由此而來的被創作的不同部分存在。第三個不能理解的因素是一個完全的異域審美。王致誠在他的敘述的每一個開始強調:“我將高興地試著給你一個這樣的描述:能夠給你一個精確的觀念。但是這太困難了,因為那跟我們的樓房和建築方式完全沒有關係。僅有眼睛能夠抓住它的真實觀念。”歐洲人對圓明園的表達風格和模式是如此不熟悉,以至於不可能透過相似性或熟悉性的關係來描述。人們不得不眼見為實。
這些多餘性、豐富性和差異的主張混合,另外給與王致誠精確的像檔案似的清單一個驚喜的氛圍。這一氛圍偶爾變成神秘化。解釋為了使樓房的進口和樓梯模糊的自然石塊的使用,王致誠陳述道:“沒有什麼如此像那些難以置信的仙人般的宮殿那樣,人想象在沙漠中央攀登岩石……”
他驚歎這個建築群僅僅20年就建成了(有一點誇張),他說一群有限的工匠卻能立即把原材料變成樓房。他評論道,人們將說:它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宮殿之一,它透過在一個美麗的山谷裡或山頂的魔法突然成形。圓明園是如此的迷人,以至於王致誠對地表的造園技術和裝飾,能夠幾乎是褻瀆地陳述:“它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天堂。”
如此魔術般的隱喻,被馬嘎爾尼勳爵在他1793年出使中國時重申,也被1860年法國和英國的掠奪者們重申。這在煽情主義者們19世紀的東方主義話語傾向中成為一個共識。但是,王致誠強調:超越這個神秘的異域主義,來製造一個對宮殿的內部邏輯和審美的不同尋常的深刻理解,是獨特的。
比如,他特別有意識地鑑定他自己在品位方面的改變。他陳述道:“我非常喜歡這個國家的樓房的式樣。自從我來到中國,我的眼睛和鑑賞品位變得有點像中國人。”他的觀點是相對主義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鑑賞品位和習慣。”儘管他維護歐洲建築的尊嚴、美麗和舒適,他從來不承認在中國人的眼裡,不習慣這樣的建築。它們像很多岩石中的洞穴,儘管歐洲的街道看似狹窄,但山谷穿過令人生畏的山川。
王致誠似乎真心地欣賞“不對稱美”和“美麗的無序”,這些是圓明園設計的基礎,與歐洲的風格形成強烈的對比。他的解釋是徹底的:“每一件東西都基於這樣的原則:它是一個鄉土和自然村莊的代表,一個獨處之地而不是一座所有按對稱和關係原則排列的宮殿。”
與自然的非對稱性原則相關,王致誠如此細緻地描述多樣的形式。他把中國對多樣性的表達不僅擺在與歐洲同等的地位,還認為它是優越於歐洲的。經過幾段描述,他下結論:“中國人給予他們的樓房,正是在這樣巨大的多樣性中。我欽佩他們富於創造力的精神。我傾向於相信與他們相比,我們是貧瘠的和缺乏獨創性的。”王的裝飾和煙火也是優越的,正如王致誠所說:“絕對超過我所見過的義大利和法國的任何東西。”

對王致誠來講,圓明園不是簡單的、被貶低的異域的東西,而是一個選擇性的帝王文化的真實的、富有活力的模型,一個有邏輯性的排序,但不同於歐洲的帝王文化,它佔有一種同樣的宇宙審美。
達到這樣一種歎為觀止的跨文化欣賞的狀態,必須校準王致誠的描述部分。他繪製圖表,對他的讀者來講第一次比喻熟悉的旅程,然後把圓明園與歐洲的鑑賞品味、技術和追求比較。當繪製地理草圖之時,隱藏在這一系列比較之中的反映似乎明確。除了與多爾相比,王致誠把北京紫禁城的規模與第戎的宮殿相比。他說圓明園:“它離北京的距離不遠於凡爾賽宮離巴黎的距離。”
到1770年,更有意義的類似物被如此地認可,以至於法國耶穌會士反覆稱圓明園為“北京的凡爾賽宮”。另外一些因素沒有被認可,但是更具系統性:當注意到歐洲人注重的建築的對稱性在紫禁城和其它一些官僚和貴族的建築中反覆實踐;當驚歎於紫禁城如何用中國、印度群島和歐洲所有的最豐富、最美麗的東西裝飾;當評論道僅有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統治者能建立如此一座巨大的建築群。王致誠認為這在中國和法國的朝廷社會是普遍的,都是統治權的含義和政治權威的文化表達。

正是這兩座宮殿藝術體系文化目標的基礎的對稱性,促使歐洲人模仿這被王致誠概述的異質的審美原則,在廣泛的中國工藝品運動中將它們重新展開。正如在學術性的文學中所確立的,審美對花園設計的影響是最大的,尤其在英格蘭。在那裡,王室的宮殿和藝術資助系統與法國不同,但是同樣的貴族精英文化的結構原則和政治被運用。
英格蘭最早的革新者們,威廉·藤比(1628-1699年),約瑟夫·阿迪生(1672-1719年),亞歷山大·波普(1688-1744年),威廉·肯特(1684-1748年)和朗瑟羅“能幹”·布朗(1715-1783年),所有人都發現:中國花園設計原則對古典主義的對稱和形式是一種受歡迎的選擇。不規則性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式審美體系的主要原則。他們明確地把它與中國的非對稱性、多樣性和鄉土性原則聯絡在一起。藤比在1685年的論文中首次提出著名的被稱為“薩爾瓦迪”的理論。儘管在英格蘭,按藤比所寫,美麗建立在“特定的比例、對稱或一致性”基礎上,中國人蔑視這種理論,獲得一種替換性的美麗,“沒有秩序或部分的排列,這些被普遍、容易地觀察”。

英國使用的蜿蜒曲折的道路,不規則的湖泊和建築裝飾,沿著這一意圖在一個公園裡創造一個連續的景觀,這所有的都受惠於、或者至少與像中國花園的早期敘述所折射的中國模式共鳴。沃壽·拉維走到這樣的程度,斷言:如圖畫般美麗的景色(所見、所代表的所有普及模式)的整體發展,都有它的受中國影響的來源,把所有的路拉回藤比1685年的文章中。
正如他所下的結論:“當規則、簡約、一致性和容易的邏輯理解的觀念第一次公開受到責難,現代鑑賞品味的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達到了……在英格蘭,無論如何,拒絕這種假設似乎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普遍被認為是首先源於中國藝術的影響和例子。”範國忠同樣顯示中國的花園如何被理解為一種自然超越巧妙的模式,沿著哥特式的風格部署,它伴隨著一種幾何式的古典主義的平衡力。伴隨著19世紀日益增長的帝國主義者們的壓力,歐洲人重新把中國的造園藝術解釋為矯揉造作的和頹廢的,但是它在整個18世紀保持了被認為是有靈感的狀況。
[原著]
格瑞﹒托馬斯
[翻譯]
尤 李
[編輯]
付 懷 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