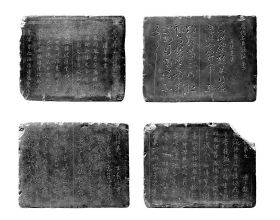今年是著名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誕辰140週年、逝世50週年,也是故宮博物院老院長馬衡先生誕辰140週年。兩位大家都是故宮博物院的元老,都視文物為生命。戰爭年代,他們不惜赴湯蹈火,全力護持。兩人數十載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同樣頗值一書。
徐森玉和馬衡都是老北大。徐森玉於1914年3月以教育部統計科長兼秘書的身份出掌北大圖書館館長,前後近三年時間。馬衡則於1 917年8月,應次兄馬裕藻的推薦,從上海來到北京,就任北大國史編纂處徵集員等職,後來主講金石學,並負責國學門的考古學會。
緣起金石,共主故宮
1921年,徐森玉和馬衡一起參加以易大廠為會長的金石組織——冰社,於是關係更加密切。兩人都有金石碑刻方面的強烈興趣和愛好,尤其對漢魏以來石經文字非常留意,大肆蒐羅有關資料。1922年冬天,在洛陽故城發現魏正始石經殘石,引起學者巨大關注。翌年7月,兩人為此聯袂去洛陽考察漢魏石經出土情況,並一起收得殘石兩百餘塊。1924年冬天,兩人再度赴洛陽考察太學遺址,繼續尋訪石經的蹤跡。一直到晚年,馬衡還在整理有關石經資料。所以,當年王國維、羅振玉乃至神田喜一郎等專家學者關注並研究漢魏石經,均得到徐森玉、馬衡兩人的支援和幫助。
1924年,馮玉祥進京驅逐溥儀出宮。徐森玉和馬衡包括他的老師寶熙以及羅振玉等人都是“清室善後委員會”成員,負責點查清宮文物。第二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馬衡和徐森玉順理成章都成了故宮的成員。1928年,他倆又是北京“文物維護會”的主要骨幹。
到了1933年,馬衡榮膺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兢兢業業,一直做到1952年為止。徐森玉經馬衡提議,也自當年7月就任故宮古物館館長,一直到1949年,即使徐老多年不在故宮,後來又定居上海,但這個位置馬衡一直為他保留著。1949以後,馬衡一度想挽留徐森玉回故宮任職,鄭振鐸甚至也為他在國家文物局留了一個文物處處長的位置,但徐因故不願回北京,轉而就職上海市文管會,馬衡只好作罷。
不辭辛勞,護寶南移
馬衡和徐森玉兩人和衷共濟的友情,在抗戰期間故宮文物的南遷時,更顯珍貴。當時文物南遷分南北兩路,過程極艱辛。馬衡和徐森玉等故宮同仁為了運輸和保管的安全,一路殫精竭慮。為了北路文物內遷至成都,1938年5月間,徐森玉與馬衡曾一起赴成都勘選庋藏文物場所,最後選定成都東門大慈寺為倉庫,後又遷至樂山等地。南路文物運到貴陽存放後,徐森玉一度又奉馬衡院長的指示,為計劃文物運滇事,於1938年9月從貴陽乘車去昆明,接洽尋找合適的存放地點,計劃後因故取消,文物轉移至安順華嚴洞,方得安定下來。就在那年初冬,徐森玉在昆明一次訪古途中跌傷,造成大腿股骨骨折,休養了四五個月才痊癒。
因此那一年,徐森玉“春入蜀,夏入陝,秋入黔,冬入滇”,可以說是他最忙的一年。馬衡為此特別寫了一首詩《七用寺字韻寄贈森玉》,稱讚徐森玉(還有莊嚴)在貴州安順山裡看守國寶的情形:華嚴洞外華嚴寺,中有高人隱姓名。壁藏典籍效伏生,避秦寧與桃源異。山高雖遜蜀峨岷,亦有流水聲誾誾。苗夷村落雜三五,耕田鑿井民情馴。山居幾欲忘年載,掃地焚香觀自在。談玄坐上有莊生(謂尚嚴),時共披圖讀山海。昔君作賦似馬卿,馳譽京華朋輩驚。於今恬退捐筆札,始信可名非常名。
字裡行間,馬衡對徐森玉不辭勞苦,安心守護故宮文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不顧安危,搶救國寶
徐森玉能者多勞,除了處理故宮的事情,還要負責北平圖書館乃至史語所等方面諸多事務。比如,當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獲得的萬餘枚居延漢簡,在七七事變爆發後,也是徐森玉冒險潛回天津,與北大助教沈仲章一起偷偷將它們搶救出來,輾轉運往香港的。
1940年,他又奉教育部之命,隻身從重慶回到上海,負責將上海文獻儲存會暗中收購的大量善本圖書點查運輸,轉移到香港等地。這樣,自然而然,他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乃至杭立武、朱家驊等上層人物走得近了。馬衡為此覺得不是滋味,因馬衡對傅斯年的“飛揚跋扈”尤感不舒服。傅斯年,人稱“傅大炮”,為人處世雷厲風行,很不講情面,正由於他的精明強幹,史語所即使在戰爭環境下也辦得有聲有色,卓有成績。但這樣的火爆脾氣,難免會得罪“左鄰右舍”。
抗戰期間,徐森玉從北京搶運出來的那批居延漢簡,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為國內外史學界所矚目。1927年,中瑞曾組織過一支西北科學考察團,1930年,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調查發現了這批漢簡,共有一萬多支,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徐森玉和馬衡以及地質學家袁復禮、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兩兄弟等人都是考察團理事會的常務理事。
這批漢簡被發現後,起初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由馬衡帶著勞幹、賀昌群、向達和餘遜四位青年助理曾進行研究,但還沒有等到及時整理出版,日本人就打進來了。
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人佔領北京,據當事人沈仲章回憶,為了這批漢簡,“當時大難臨頭,一部分師生已紛紛逃散,我只好向當時北大秘書長鄭天挺請示,他不敢表態。我又去找尚留在北京的西北考察團理事沈兼士、袁同禮等,他們也怕風險,不敢表態。對這批木簡有感情、有責任心的人如徐森玉、傅斯年等人又都不在北京……”
沈仲章當時只有三十歲出頭,是北大教授劉半農的助教。因沈仲章參與整理這批木簡,他冒著風險把木簡先偷偷搬出北大,轉移到徐森玉的住處。隨後又乘火車將它們運到天津,並寫信給時在長沙的徐森玉報告此事。徐得知訊息,馬上向傅斯年報告,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援下,徐森玉到天津和沈仲章接上頭,兩人隨後不顧風險,一起成功地將漢簡輾轉運到香港。從敵人眼皮底下搶救出千年國寶,這在當時震動很大,非常鼓舞學人計程車氣,徐森玉和沈仲章此舉也為國家爭回體面,意義非凡。
剛正不阿,堅守故土
1949年2月,蔣介石撤退大陸前夕,章士釗與邵力子、江庸、顏惠慶四人到北京參加和談,有潘伯鷹隨行。21日那天,馬衡訪邵力子等人於北京六國飯店,並一起午餐。
徐森玉和馬衡都不贊成文物運中國臺灣,為此兩人都曾採取消極拖延甚至不合作的態度。因為徐森玉精鑑別,當時為文物運中國臺灣,上面指定他為押運負責人。據說為此還許諾,到臺後給他故宮博物院院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職位。但徐森玉躲在上海,託病遲遲不動,後來只好由李濟負責文物全程運臺事宜。
馬衡畢竟有君子風度,當聽到潘伯鷹帶來的徐森玉傳話,1949年9月13日,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徐森玉,當晚還與鄭振鐸、趙元方等人為徐老接風洗塵。在京期間,兩人多次見面,相談甚歡。馬衡一直想勸說老友仍留在故宮工作,但徐老因家庭等原因堅持回滬,馬衡也只好不再挽留。
此後兩人的交往,尤其像一起南下到澳門,從香港收購“二希”(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迴歸等故事,眾所周知,這裡就不多說了。
1955年馬衡去世,他的遺稿《漢石經集存》由陳夢家整理編輯,徐森玉親為老友題簽,於兩年後出版傳世。馬衡早年曾刻“漢石經齋”印贈送徐森玉,故後人為他收集文字,也以《漢石經齋文存》的書名結集出版。漢魏石經,實在是他倆共同的友誼見證。他們一生為守護國寶殫精竭慮,移入世人對他們的評價,他們就是國之文化瑰寶。
來源: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