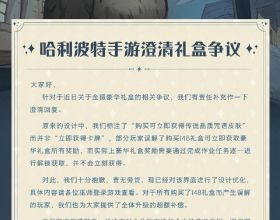—— 一個農村兵的時代際遇
■ 王承英
1979年初冬時節,湘北農村開始溼冷,晨起,會發現植被上一層淺白色的霜凍,人們稱為“打霜”。
各公社、大隊正按計劃實施著秋冬播和秋冬修,社員們也在做一年中的最後衝刺,盤算著多撈些工分在年終結算時當“進錢戶”。
我領到了大紅的入伍通知書,只等著應酬完叔叔、姨媽和其他親戚們殺雞、趕場準備的歡送家宴,便隨著接兵首長遠行。
告別家鄉民辦教師的崗位,我來到三國古都——河南許昌服役,在那裡度過了5年軍旅生活。那些烙下時代印記的奮鬥經歷、人生際遇,至今仍揮之不去,歷歷在目。
從湘鄂邊到中原地
從我老家湘鄂邊界的湖南省澧縣復興鎮曾家村,到我從軍的河南省許昌市八一路的軍營,相距700多公里。如今的交通條件,車程大約為8個小時。而42年前,我揹著揹包,帶著幾本心愛的書籍,跟著接兵的首長,坐汽車、搭擺渡船、上輪船、乘火車,從老家出發到軍營,硬是耗了4天時間。
1979年12月3日上午,我們澧縣籍(不少是來自夢溪區下轄的6個公社)500多名新兵在澧縣澧澹公社擁憲大隊集結後,下午統一在津市(當時屬澧縣管轄的津市鎮,現為縣級津市市)住下。當晚,我們統一組織在津市影劇院觀看電影《偷腳踏車的人》,這是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國門剛剛開啟,新兵們第一次過“洋癮”。
4日凌晨,我們在津市碼頭坐上運兵輪船(途中由單層換為上下兩層),陸續經過澧水、沅水、資水、湘水4條水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去1年時間,改革開放剛剛啟幕,還難得見到“今朝更好看”的景象,一切仍顯沉寂。河流兩邊是一望無際的蘆葦,沒有一座橋樑,輪船上的桅杆再高也不會受到阻隔。白天,河流兩岸見不到車流和人影,夜晚,除依稀可見的航標燈外,幾乎一片漆黑。
當晚12點,我們到達長沙水運碼頭,下船步行到長沙火車北站,稍作休整後,後面2天全是在悶罐車上。
就是這個悶罐車,我“享用”了2天,卻記了它40多年!
悶罐車又稱代客車,是利用鐵路柵車代替客車運送人員的車輛。使用悶罐車運送人員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在鐵路客車數量不能滿足大規模人員輸送的情況下產生的。美軍和蘇軍在二戰期間開始使用代客車運送部隊。我國使用代客車始於1948年遼瀋戰役。在我軍歷次重大軍事行動,特別是歷年的新兵運送鐵路運輸保障中,悶罐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放後,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部隊保障能力提升,悶罐車漸行漸遠。從1986年開始,運送新兵一般不再使用它。2007年底,國家鐵道部和解放軍總後勤部發出通知,從2008年元旦起,鐵路軍隊運輸不再使用悶罐車,升級為普通客運火車。
我乘坐的那列悶罐車是木牆木底,內部設有床託,可搭設床板,沒有車窗,通風換氣全靠車廂的木板間隙。我清楚地記得,那列悶罐車上有沖鼻的牛糞味,估計在我們乘坐之前曾運載過牛羊一類的牲畜,以至於第一個晚上大家久久不能入睡。
悶罐車的確不舒適,但在悶罐車上的2天時間裡,我卻學到了知識,聽到了趣聞軼事,頗有些新奇感。
北上途中分別經過城陵磯、孝感、信陽3個兵站並停留,主要是解決用餐。這裡的飯菜很合大家的口味,特別是那個大白菜炒紅薯粉,另加一點肥肉,簡直是美味,成了我後來幾十年的“保留菜”。
每當兵站喊“開飯”,大家便健步如飛,這時,帽子擠掉在飯桶裡的、揹包擠散的、鞋子踩脫的,甚至發生爭執的,時有發生。那天中午,在信陽兵站下車就餐,大家一窩蜂朝著飯桶跑過去。我趁著人群縫隙鑽到了飯桶邊上,用力操起勺子盛滿了一大碗飯,好有獲得感!這時,接兵的班長跑過來很認真地告訴我:“你這方法不對,第一碗飯要盛少一些,可以快速吃完趕在前面盛第二碗,即使吃得下第三碗,你仍然會排得上,因為你錯開了大家盛飯的‘峰值’,聽我的沒錯!”還沒正式到達部隊,我就跟著老班長學了一招。
1979年12月6日傍晚,經過4天顛簸,我們好不容易到達了許昌。
許昌歷史文化悠久。東漢建安元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洛陽殘破”為由遷都於許昌,即稱許都。這裡至今還儲存著曹丞相府、漢魏故城、受禪臺、春秋樓等許多歷史遺蹟。
這個中原腹地的北方城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清一色的用麥稈糊著泥巴築就的圍牆和同一個模樣的二到三層的灰色房屋。由於年代久遠,也由於中原地區泥土缺少黏性,那些麥杆圍牆早已東倒西歪了,與現在許昌高樓大廈下面拆違透綠、花團錦簇的景象相差萬里。
在許昌火車站一個不大的廣場,開始分配新兵。聽著首長點名,我們幾百號新兵歸到了前來領兵的各分隊首長面前,隨即坐著汽車到達各自的新兵連。
那些難忘的場景
當兵之前,我在澧縣雙龍公社聯校擔任2年多中小學民辦教師。民辦教師又稱“赤腳老師”,雖然跟公辦教師一樣行使職責,但仍然是農村戶口,透過比照農村勞動力拿工分獲取報酬,另外每月領取國家發放的5元補貼。跟拿國家工資的公辦教師一道工作,待遇和身份卻有明顯差別,民辦教師總是有些自卑感。
有個真實的事情。當年一個民辦教師表現優異,公社黨委的領導激勵他說:“你要繼續努力,爭取年年當先進,到時我們提拔你去當營業員。”民辦教師雖然算半個知識分子,但社會地位可見一斑!對我來說,吃上“國家糧”,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由國家統一供應糧食指標,當上國家幹部職工,才算是解決根本問題。要想這樣,當兵是條重要出路。
一年一度的冬季徵兵開始了,我積極報名,按應徵程式,在澧縣夢溪區區公所做完體檢,由公社武裝部和大隊黨支部完成政審併合格後,卻遇到了年齡障礙。當年徵兵政策規定,應徵青年系農村戶口的須年滿18週歲,城鎮戶口的須年滿17週歲,為此,我將年齡填大了一歲,以至於後來,我的檔案年齡還以此為準,得提前一年退休。
農村青年參軍,其家庭還有優待。當年在澧縣農村,現役軍人家屬每年補貼280元錢、400斤糧食,還有精神上的榮耀和政治上的光環。比如,我家門前就掛上了“光榮軍屬”的牌匾,“一人當兵,全家光榮”的標語貼在我家土牆上,特別醒目。為了安慰那些沒有當上兵的青年,公社和大隊會掛出一副很有意味的標語:“當兵光榮,當民兵同樣光榮!”
我所在的部隊是一支身經百戰、出生入死的老部隊,是楊根思生前所在部隊,朝鮮戰場上攻打長津湖的“冰雕連”也出自這支部隊。我們到達軍營時,部隊剛剛從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班師回營。全師上下正以剛結束的慘烈實戰總結研究戰法、訓練法,作風紀律、軍事訓練都抓得特別緊。
一次訓練時,我的手套不小心弄丟了一隻,一隻手在冰天雪地上裸露著,凍著也不能補上,自己買也不行,因為部隊規定,不能使用民用服裝,短褲都得穿統一發放的,何況手套是露在外面的,看得見,不統一會影響整齊劃一。本來我們從南方來到北方就有些不適應,加上那個冬天格外冷,半個月下來,我的右手中指沒戴手套凍爛了,流著血水,看得見骨頭,如今還留著疤痕。
啟程去部隊時,父親把他用多年積攢下來的60元錢買下的“青島”牌手錶送給我作紀念,可一到部隊,就因有規定不許戰士戴手錶而被連首長收走了,直到2年後我當了班長才歸還我。
我所在的師直警衛連,按上面規定是半訓分隊,但連隊首長認為,我們在師首長身邊工作,半訓分隊也要與全訓分隊爭高低,多項訓練指標都在全師名列前茅。在“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口號下,連隊訓練熱火朝天,爭分奪秒。比如出操,不是簡單的跑跑步、完成幾個單雙杆動作便可以完事,而是每天全副武裝、坐上汽車去到5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後把車開走,我們再全副武裝跑回來,而且限定時間,沒半點取巧的辦法。
直工科的首長們
我在師直警衛連訓練生活2年後,師司令部直工科將我借調去代理新聞宣傳幹事的工作。賞識我的伯樂是吳昌雲,安徽蕪湖人,1964年當兵。他剛從通訊營教導員提升為直工科科長,成為副團職幹部,工作勁頭很足,一心想把直屬分隊的工作推上新臺階。透過多方物色,他了解到我當兵前教過2年多書,而且字寫得好,還在家鄉省報發表過新聞報道,於是把我挖了過去。
借調到直工科後,我的工作表現更突出了,不能辜負首長的知遇之恩啊!科裡的重要材料均由我拿初稿,師直屬分隊的業績、經驗做法也因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調查採訪、精心寫作,多次被《解放軍報》《戰鬥報》和《河南日報》報道,我也經常被科長表揚。
1980年5月10日,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聯合發出了“關於選拔培養基層幹部問題的通知”,軍隊幹部制度進行了重大調整,軍官提任必須經過院校培養。這對我很不利,因為當時部隊戰士報考軍校只有理工科專業可選擇,那就只能按照理工科課程組織考試,沒有任何文科專業招收戰士學員,正巧我是文科生。這個政策革了我的命,直接提幹被封了門,報考軍校又不對口。我這個備受關注的“幹部苗子”前途渺茫。那幾年,我拼命工作,也著實為自己的去向苦悶、煩惱。
毛武金是科裡的幹部幹事,浙江人,1968年兵,工作很細緻、原則性很強,也很關心人。他不止一次對我說:“小王,你的工作,首長和同志們都很滿意,要相信組織,也要正確對待自己的前途。”我感覺,這既是鼓勵又是安慰,但我最關注的提幹的事卻從他那裡聽不出什麼資訊。有一天,毛幹事又說:“師首長和吳科長都很關心你成長進步的事!”這句話倒是讓我聽出點希望來了,但也不知道希望在哪。
一天下午,科裡其他同志下到直屬分隊調研,留下我看家整理材料。3份對上級幹部部門的報告映入我的眼簾,報告抬頭分別是武漢軍區政治部幹部部、20軍政治部幹部處、58師政治部幹部科,標題均為《關於破格提升王承英同志為幹部的報告》,時間跨度為1981年12月到1983年12月。2年裡,以科長為首的同志們,為我做了這麼多努力,而且一直瞞著我,沒洩露半點,我感動地流下眼淚。當然,這是秘密,我只能裝著沒看見。我也知道,這些報告再誠懇、再執著,陳述得再合情合理,也沒有多大可能讓我穿上“四個兜”,但大家這麼認可我、幫助我,我從內心深處感激他們。
多年過去了,我一直記著、念著我的科長吳昌雲(後轉業到安徽省蕪湖市委紀委,已退休)、幹事張道發(後擔任過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少將,已在北京退休)、幹事金方富(後轉業在湖北省仙桃市,已退休,女兒金婷婷為著名歌唱家)、幹事毛武金(後轉業在浙江,已退休)、參謀陸紅星(後轉業在江蘇,已退休)、幹事鄒良初(後轉業在江西豐城,已不幸病故)。
2000年春,我率隊在安徽考察,專門到蕪湖看望吳昌雲科長。老科長帶我在剛開通的蕪湖長江大橋上走了一個來回,足有4公里,越走越來勁。老科長的愛人王大姐說:“承英,你來了,老吳特別高興,回地方這麼多年,他經常念起你,說你沒能在部隊提幹太可惜了!他身體不好,平時散步走上幾百米便上氣不接下氣,今天是個奇蹟!”
一個電話擊碎軍校夢
1984年,武漢軍區為了彌補軍校招生在專業設定上的不足,並留住在新聞宣傳方面有專長且業績突出的戰士,經解放軍總政治部同意,決定與信陽陸軍學院合辦新聞班,在全軍區各部隊推選出合乎條件的戰士參加特設專業的招生考試,考試內容為文史綜合和新聞業務,根據文化成績和工作業績(主要是發表的作品)綜合情況擇優錄取。
通知一到師政治部幹部科,我第一時間知道這個訊息,按招生條件逐一對照,自己完全符合且有一定優勢。於是,我抓緊準備文化考試,整理發表的作品,大多是訊息、通訊、言論等,並很快填寫了報名表。
7月20日左右,我們約40名從全軍區各部隊推薦出來的骨幹集中到武漢軍區政治部招待所參加文化考試,共2門:文史綜合和新聞報道業務。考試一結束我就為自己估了分,每門均應在85分以上。
接下來便是靜待訊息。
這一次招考對我太重要了。當時,義務兵服役年限為3年,我已經服役5年,屬超期服役,而且已年滿22歲,即使以後軍校有從戰士中招考文史專業的機會,按照23歲的限制,我的年齡也不允許了。
大約8月5日前後,師政治部幹部科告訴吳昌雲科長,說王承英已被信陽陸軍學院新聞班錄取。那一陣,我的激動、興奮可以說許多年都沒有過。接下來,我一邊在科裡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一邊做著上學的準備。我有輕度近視,便做些眼保健操,以便讓上學後的身體複查能順利透過。為打好揹包收拾好行裝,又請通訊營的老鄉戰友找來一包線纜。
我時不時沉浸在美好的遐想當中。小說《高山下的花環》開篇語“位卑未敢忘憂國”讓我深受教益。然而,我上了軍校才有繼續奉獻國防的機會,憂國才能落到實處。過去在舊社會,弟兄3個至少有1個當兵,而我兄弟4個,我出來當兵,也該當得有模有樣。上了軍校,離自己的理想會更近些。就我來說,再也不用去領12元1個月的津貼,拿著50多元的月薪,而終於可以為偏癱的奶奶盡點孝心,寄些錢買上她特別愛吃的“包面”(湘北農村對餛飩的稱謂),為正上中小學的弟弟妹妹支援學費,還可以去新華書店挑選自己喜歡的書。
8月20日前後的一天,吳昌雲科長沮喪著臉找到我,說:“小王,你要正確對待自己的成長進步!”科長突然蹦出這麼一句話,我感到一定有什麼不好的事,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信陽陸軍學院來電話告知師幹部科,新聞班不辦了!我頓時無言以對,呆立了許久。
師首長給學院領導打電話發脾氣,說怎麼能把戰士的前途當兒戲,可這又有什麼用呢!的確,這樣極不負責任的事情的確極其罕見,令人難以置信。後來,我多次打聽錄取取消的原因,大致是,當時有好幾個軍隊首長的子女要求上這個班,但不合乎條件,有關部門和學校頂不住,也擺不平,又正值全軍各大單位開展整黨運動,擔心搞出麻煩,於是簡單行事:不辦了!
本來,我急匆匆來部隊當兵,就錯過了一次已經錄取上大學的機會,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斷了!
軍營南邊的圖書館阿姨
當時許昌市城區並不大,文化地標也不多,地區、市和縣的3家圖書館算是公眾知曉度最高的文化場所了。部隊在市區中心偏北的位置,每逢週末時間和節假日,我去的最多的是部隊南邊的圖書館。
我去的這家圖書館,當時全館藏書不到10萬冊,有200多種報紙期刊,共五六個工作人員。比我目前的私家藏書多一點,但那個時候,這些資源對我來說太珍貴了。
每次,我都會邀上早我一年入伍的湖北江陵籍戰友吳順新(書法愛好者)一同前往。我們去圖書館的目的很明確,查閱資料,做學習卡片;尋找發表自己作品的報紙期刊,我的都是新聞報道和言論文章,吳順新的則是書法作品,同時再發現一些與自己的作品相吻合的報刊,以便精準投送。
在圖書館,我們打交道最多的是40多歲、中等個頭,嚴肅但也熱情的李阿姨。為了求李阿姨為我們提供便利,我們沒少“投入”。每次到來後會主動打掃衛生,整理報刊書籍,搬運笨重物品,還有好幾次幫她寫工作總結。時間久了,李阿姨對我們印象極好,圖書館就像我們自己家開的一樣,可以隨便查閱,隨便抄錄。
李阿姨總是像長輩一樣噓寒問暖,我們的交流也越來越多。她對我的家世、個人情況瞭如指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李阿姨關心上了我的個人問題。一個早春的週日上午,她把我叫到一個安靜的角落說:“你是農村入伍的,退伍得回農村,如果找個許昌城裡的姑娘結婚,不僅不用回農村,還可落戶許昌安排工作。”儘管我早就知道這個政策,但我還是從內心裡感謝她的提醒。
從此,幾乎每次去圖書館,她都會向我提起找物件的事,後來,她對我說,已經物色了一個家境很好、條件也與我很般配的姑娘。我一邊感謝著她,一邊解釋說:“我年齡不大,暫不考慮,以後也不打算在這邊成家。”李阿姨說:“你先別回絕我,好好想一想,姑娘條件很好,而且對你滿意,也不嫌棄你老家是農村的,這種機會難得!”
這麼一說,難道姑娘認識我?
新的一年元旦節,我帶著卡片、筆記本再次來到圖書館。一進門,李阿姨就問道:上次說的那個事,你想得怎樣了?我說:“感謝您,我還是暫不考慮個人問題。”她說:“我不是要你感謝,是為你的人生著想,勸你還是答應這門事!”她又將姑娘本人及其家庭情況再一次詳細講給我聽,憑直覺,我斷定這姑娘就是她女兒,就是那個經常來圖書館,笑容可掬、瓜子臉、長髮、身材姣好,穿著紅色風衣,總是笑盈盈地幫我們找報刊書籍的姑娘。
姑娘的模樣確實讓我心動,但考慮到地域因素,我還是保持了一個年輕人難得的定力!我委婉地謝絕了李阿姨,但她要的不是“委婉”,而是一個肯定的答覆!
幾個小時過去了,我要離開圖書館。李阿姨走過來很認真地說:“我們圖書館是地方開辦也是為地方使用的,沒有為部隊開放的責任和義務,以後,請你不要再過來了,這是規定。”她把“規定”兩個字說得很乾脆。
我十分清楚李阿姨這個“規定”出臺的來由,但我不埋怨她,我沒有領受她的好心,應該受這個懲罰。
那年月,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很大,城鄉之間聯姻的事極為罕見。李阿姨的內心肯定想:我城裡的千金小姐能看上你這個農村兵,已經衝破世俗,而你卻不識時務。
離開許昌37年了,我一直記得李阿姨。算起來,如今她老人家應該在80歲上下,如果健在,祝她幸福快樂;如果已經仙逝,願她不朽!
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在想,我是不是有點像路遙先生筆下的高加林、孫少平?拙文的意蘊是不是有點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只不過我記述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而路遙先生的作品是文學;我的是區區小文,路遙先生的是鴻篇鉅製。
然而,我們記錄的同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共和國發展中的時代景象、歷史變遷,同為這片土地上生命個體的奮鬥和喜樂悲傷,是我們前行的足音回放。
但願這篇寫真文字能喚起人們對過去歲月的記憶,在回味中激發奮進力量,走好人生的路。
本文原載於《時代報告》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