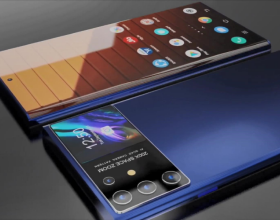看點 如今,越來越多的歐美民眾被“政治正確”所綁架,甚至一度殃及教育界:教授“因言獲罪”,文學鉅著被直接刪除……而在學校錄取等頗具公平爭議的問題上,追求表面的“正確”,實際是在逃避解決問題,治標不治本。對孩子來說,他們需要具備換位思考,理性做決定的能力。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具備這樣的能力,校園才能變成一個求真知的地方,他們才會更有精力去解決“不公平”問題的根源。
支援外灘君,請進入公眾號主頁面“星標”我們,從此“不失聯”。
文丨Luna 編丨Amanda
11月上旬,華納確認,J.K.羅琳本人將不會參與《哈利·波特》電影系列20週年回顧展。由此,“羅琳被《哈利·波特》除名”的新聞再度刷屏。
去年,羅琳就因為推特上部分關於跨性別者權益的發言而被“除名”。
反對她觀點的人認為,“羅琳在歧視跨性別者”,“她的言論損害了跨性別者的權益”。其中也不乏哈迷,為了表達自己的主張,他們刪除了《哈利·波特》粉絲網站上關於羅琳的資訊。
從此,網路及現實中對羅琳的攻擊就不曾停止。
11月中旬,羅琳在推特稱,迄今她已經收到了無數死亡威脅,一些人還透過照片洩露了她的家庭住址,但她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
“羅琳被除名”事件因“政治正確”而起,至今未平的餘波讓人不難聯想到近年來同樣由“政治正確”話題引起的一系列新聞:
去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的一名教授,在課堂上提到中文會使用“那個”一詞,學生認為他此舉侮辱黑人學生並舉報。隨後,學校“暫停”了他的工作。
今年,加利福尼亞州的數學教學改革提案中,曾引用題為《公平數學教學的方法》的報告,該報告拒絕承認孩子有數學天賦的差別,並且認為數學有正確答案是一種種族主義。風波過後,提案刪除了有關這項提案的引用。
同樣是今年,英國著名的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課的學生投訴莎士比亞的作品“充滿了白人男性的經驗”,學校為了“去殖民化”,選擇從課程大綱裡刪除莎士比亞的作品。
不可否認,政治正確最初因為弱勢群體聲張權益而誕生,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如今,越來越變本加厲的激進的“政治正確”風潮,不僅影響到了文藝創作領域,更是令教育領域也陷入瞭如履薄冰的境地。
原本應該是學習和研究淨土的校園,也時不時遭受“政治正確”風潮侵擾,越來越多的老師、教授要麼被要求離開職位,要麼明哲保身,避開敏感內容。大學學生,甚至青少年也被裹挾進去。外灘君不禁想問,教育可以應對這場風暴嗎?
說錯一個詞就可能被投訴
大學校園的教授們如履薄冰
2019年末,“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詞悄然走紅,在教育界最常見的新聞,就是某某講師或教授因為上課選用的材料、和學生交流時的用詞等原因被學生投訴,有不少人都被要求停課,甚至被開除,職業生涯都被“取消”。
其實,2018年《嬌慣的心靈》一書就指出,在此之前的多年內,大學就已經出現了一種“完全主義”的現象——學校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和包容的校園環境,開設了專門的通道來接收關於偏見、騷擾、歧視等現象的的投訴與揭發。
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提高這條模糊的界限:
把“感受”當作“安全問題”:哥倫比亞大學的“西方文學與哲學經典”課,曾將奧維德、荷馬、但丁、奧古斯丁等人的作品列為閱讀材料。但2015年有四名本科生撰文稱,這裡麵包含許多“觸發性和冒犯性的材料”,教授應該做到“事先警告”,併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心理支援。
把“情緒”當作“安全問題”:一些學校規定,教授應該使用學生所傾向的性別代詞來稱呼他們。如果學生不想被稱為“he”或“she”,就要用“zhe”或“they”,否則,就會“在課堂上有損甚或危及學生的安全”。
把“觀點”當作“安全問題”:因為不認同作家麥吉爾羅伊對美國性暴力環境的定義,有布朗大學的學生認為,讓她進入校園演講,會“摧毀一切”。這位同學還打造了一處“安全空間”,為任何受到情緒觸動的同學提供庇護與幫助。
而這些激進追求“安全”與“正確”行為的結果由誰來承擔呢?是想用心授課的講師、教授,是真心求學的學生、真正需要關注的弱勢群體,乃至整個社會。
與這些激進的投訴者不一樣的是,許多講師和教授變得越來越如履薄冰。很多教授坦言,他們是在“提心吊膽地搞教學”。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珍妮·石·格森曾在《紐約客》上發文:“在討論關於強姦的法律時,組織學生討論,挑戰並質疑對方,已變得寸步難行,於是教師開始放棄這個題目……如果性侵這個題目被驅逐出法學院的課堂,損失將是巨大的——首當其衝的就是性侵受害者。”
8月有報道稱,加州大學醫學院一位內分泌學教授給學生髮郵件道歉,因為自己用了“孕婦(pregnant women)”,而不是“孕者(pregnant people)”。這在加州大學醫學院不算特別,如果他們沒有即時道歉,學生就可能發起投訴或請願。
有人評論,生物學是科學,有無法改變的真理,無論任何人多麼想要/希望改變它們。教授不應該為教授科學真理而道歉,絕對不應該迎合一群學生,這些學生是我們未來的醫學專業人士,他們似乎無法掌握現實。
“我不希望這些醫學生中的任何一個,將來成為我或我的任何親戚的醫生。”
如果說一些人可以透過避免敏感內容,或者及時道歉繼續工作,那麼另一些普通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去年6月,蘇格蘭作家兼代筆作者吉莉安·菲利普被告知,她的圖書包裝公司與美國出版商考慮到她在推特上支援羅琳帶來的不良影響,將不再與她合作出版——她被“取消”了。彼時,她剛完成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Bravelands的第七部。
更糟的是,經紀人說,不會再有傳統出版社願意和她合作了。為了謀生,菲利普不得不考慮轉行——她開始學開卡車,和朋友開始馬匹飼養業務。一些沒有名氣的研究員、講師也可能要面對同樣的困境。
“面對大量要求解僱或懲罰一名員工的請求,附上‘否則我們將抵制你和你的公司’時,公司更容易透過解僱員工來解決問題,因為僱主總可以招到很多僱員。”美國研究機構布魯金斯學會的高階研究員喬納森·斯莫克認為,“所以‘取消’對普通人職業生活的影響往往是毀滅性的。”
在這樣的環境中,教授們不說人人自危,至少也都要過得小心翼翼。追求真理、觀點交鋒都不得不讓步於部分人追求的“社會正義”。
表面的“政治正確”
難保真正的教育公平
誰能看到亞裔的艱難掙扎
除了課堂內容、網路發言這類的“正確性審查”,教育機會公平也是“政治正確”風潮下繞不開的問題,這也是美國長久以來教育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
但是,教育機會這塊蛋糕似乎怎麼分,都難以達到每個群體都接受的結果。
比如受到許多關注的學校錄取問題。
芝加哥大學近期釋出了一篇論文《哈佛對校友子女及運動員學生的偏好》(Legacy and Athlete Preferences at Harvard),認為哈佛大學並不是百分之百地擇優錄取。
研究者發現:在白人中,超過43%是透過運動員、校友子女、院長關注名單、教職工子女(ALDC)幾個類別被錄取的;在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中,這一比例均不到16%。
他們又設定了一些限制條件,研究不同錄取政策會給哈佛帶來怎樣的影響。得到了如下的結果:
- 如果這些白人ALDC申請者走普通申請渠道,那會有75%的人收到學校的拒信。
- 如果取消校友子女或者運動員偏好,入學的白人人數都會明顯減少,而非裔、拉美裔和亞裔的入學人數會增加或沒有變化。
- 如果取消校友子女、運動員,以及種族偏好,那非裔和拉美裔的錄取率會下降驚人的69%和42%。
由此可見,哈佛現行的錄取政策至少對白人學生給予了很大傾斜,這也難怪“種族配額制”,會成為解決方案之一。
但配額以後,“透明的”亞裔又再次成為受害者——“種族配額制”有意限定入學新生的種族比例,這樣一來下,就會有亞裔學生即便學術表現、課外活動都更優秀,但因為超出比例,而不能被錄取。對於個體而來,這無疑是不公平的。
這也難怪會有人認為,“平權法案”讓許多成績並不優秀的非裔、拉美裔學生進入了哈佛,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擇優錄取”。“公平入學”組織也在2014年指控哈佛大學在招生中歧視亞裔學生。遺憾的是,最終美國聯邦法院裁定哈佛大學沒有歧視亞裔申請者。
這種流於表面的“政治正確”,治不了根子上的教育不公平。同樣的錄取難題也存在於紐約的9所特別高中,各個群體也依舊為教育機會吵得不可開交。
剛才提到的這些特別高中都以出色的學術表現、畢業錄取情況出名。透過按分數擇優錄取的特殊高中考試(SHSAT)制度,占人口24%的亞裔獲得了特殊高中62%的名額;占人口45%的非裔和拉美裔在特殊高中只佔10%。
亞裔成了特別高中的大多數,非裔、和拉美裔佔比很低,這個比例好像不是很“正確”。於是,紐約市長在2018年公佈了針對特別高中的“多元化改革計劃”,準備分兩步逐漸提高非裔和拉美裔學生的佔比,最終取消現有的SHSAT制度。
這對向來重視教育的亞裔家庭無疑是重大的打擊,有不少家長公開表示,這項貌似為了“讓各族裔平等”的改革,本質是對亞裔的歧視。
今年紐約特別高中公佈錄取結果以後,關於錄取公平的交鋒仍在持續。有報道指出,超過一半獲得錄取的亞裔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改變SHSAT制度是在無視這些弱勢學生的努力。
也有議員參選人說,有人看到亞裔獨佔鰲頭,心理不平衡,就重提廢除考試,其實非裔、拉美裔表現不好,和考試沒有關係,考試本身最公平的。
紐約華裔黃先生更是直指問題的源頭:“紐約教育局的心思沒有放在辦好學校、提高教育質量上面,而是一直拿‘種族’說事。取消SHSAT、取消天才班,又推抽籤,推多元化,把學生從原來對應的學校轉到別的學校。今年非裔、拉美裔報考人數、錄取人數都有所下降,說明不重視教育質量,結果只會越來越糟糕。”
一邊是透過種族配額,達到資料上的“公平”,另一邊卻放任真正的歧視橫行校園。韓裔作家Wesley Yang曾在Paper Tiger一文中寫道:“Jenny Tsai曾在競爭激烈的紐約公立學校亨特學院高中擔任班長的學生,她常會聽到有人說:‘學校的亞洲人太多了,早晚把學校搞垮。’”
高中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早就被提及的亞裔在職場遇到的“竹製天花板”。在這種現實之下,還只追求資料上的“公平”,表面的“政治正確”,無疑是在逃避解決問題的責任。
培養孩子換位思考、理性抉擇
是在給他們一個更安全的未來
現在美國各類“政治正確”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旁觀者不免會認為,吵鬧者是大多數。可2018年10月的一項調查卻給出了令人意外的結果。
這項民意調查題為《隱藏的部落:美國的兩極化格局研究》,訪問了8000名受訪者,收集他們關於美國人對各種政治和文化問題態度,包括種族、移民、性別歧視、言論自由和其他熱點共計數十個問題。結果顯示:
- 8%的受訪者可以算作激進的左翼,支援政治正確、認為政治正確不是問題的人比例最多。
- 25%可以算作保守的右翼,幾乎都認為“政治正確是個問題”。
- 67%的人屬於疲憊的大多數,很多人對美國的政治現狀感到悲觀,一些人不喜歡政治正確。
所以,其實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政治正確是個問題,並且大部分人已經覺得不堪其擾。而我們的孩子,有可能以後也會成為這大多數中的一員。
令人擔憂的是,有不少青少年已經開始著急站隊,尋求自己的同道,甚至熱衷於“取消”那些在他們看來觸及了“政治正確”紅線的人。
如果越少青少年明白“取消文化”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越少有意識先溝通理解,後下結論,那麼等待他們的或許會是一個更加“非黑即白”的環境。
所以,讓孩子學會換位思考,多理解別人的想法,再做出理性的判斷和行動,就是在給他們改善未來的環境。
首先,家長等養育者就要先警惕二元論的思考方式,比如認為“如果某件事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險”,從而因噎廢食,不讓孩子幹這,不讓孩子幹那。
要讓孩子知道,一些壓力會傷人,會讓人不舒服,但它不會殺人。
與其為孩子鋪好路,不如讓孩子學會如何走好路。讓孩子在不斷的體驗中積累成長的經驗,就是給他們最好的禮物。
比如把玩耍的時間還給孩子,讓他們能夠和玩伴們在戶外自由地探索;為了確保人身安全,成人可以看護,但不應該過多地介入孩子們玩耍時產生的爭端。
從孩子本身來說,二元對立的思考是一段必經階段,比如一二年級的孩子,看待世界就是“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但是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也會進入到具備灰度判斷的階段——他們可以開始思考兩難的問題了。這個時候,就需要家長推動他們多換位思考,體會不同視角下的觀點。
比如經典的器官捐獻問題:一間診室裡有五位需要替換不同器官的病人,已經到了不治療就無法存活的關頭。此時,一位醉漢被送進醫院,他的器官正好匹配那五位病人,可一旦取走器官,醉漢也無法存活。醫生應該作何選擇?
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家長要給孩子的思考一點助力:
我做的選擇,有什麼合理的地方?又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除了已經做出的選擇,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其他的選擇,除了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地方?
這樣的換位思考能夠讓他們意識到,這個世界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能夠看到當下一些“政治正確”事件的荒謬之處。
《嬌慣的心靈》中有這樣一段話:
簡言之,因為人類長期以來部落競爭的進化史,我們的心靈很容易出現“我們VS他們”的二分思考。但要是我們想創造友善、包容的共同體,就應竭盡所能,關閉部落主義,同時培養人之為人即有共性的感覺。
外灘君也認為,讓孩子學會換位思考,理性做決定,才能成為一個情感和性格上都真正勇敢的人。而不是透過“取消”他人,或者以“正確”為名,僅為自己打造一個“安全空間”,而忽略真正的問題。給孩子真正的勇氣,才是為他們構建一個真正安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