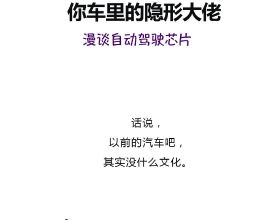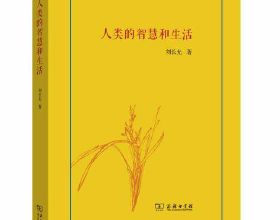來源:嘉興日報-嘉興線上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的越劇人生》 王文娟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在自傳《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的越劇人生》中,王文娟真情回顧自己的人生和藝術道路,從新中國成立前的艱難謀生到後來的潛心創作,從團隊合作打磨精品的成功經驗到響應文化體制改革的有益探索,以及關於婚姻家庭的種種真情。從中,人們得以見到一代越劇藝術大師的藝術追求和人生縮影。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的越劇人生》自2013年1月出版以來,多次再版。這本書也成為無數王派愛好者的必讀和收藏書目。
1962年夏天,當越劇電影《紅樓夢》的拍攝進入尾聲時,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與電影演員孫道臨結婚。那年他四十一歲,我三十六歲,是名副其實的大齡青年,要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標準的“剩男剩女”。
多年以來,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戲養家的責任,把弟妹培養成人之後,再考慮自己的婚嫁。從總政回到上海後的幾年內,團裡的姐妹們紛紛結婚成家,兩個弟弟也如願考上了大學。一天,我住在越劇院宿舍,晚上出來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靜,更顯得我獨自一人形單影隻。也許,在舞臺上演繹了那麼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後,我也是該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
此時,黃宗江這個“大媒”出現了,他與道臨是總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是我在總政時期的同事,可以說是我們共同的朋友。此前,同在上海文藝界這個不大的圈子裡,我和道臨也並非完全不認識。20世紀50年代我住在華山路枕流公寓,常坐門口的48路車去上海音樂廳開會,有好幾次遇見同在等車的道臨,那時文藝界常在一起開會或聽報告,碰見了也不奇怪,彼此頷首微笑而已。認識之後,我才發現他當時住在武康路上的密丹公寓,去音樂廳理應坐26路,問他為何捨近求遠,他卻只是笑而不語。
1958年春,黃宗江來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協招待所裡,玉蘭大姐陪著我,黃宗英陪著孫道臨,黃宗江很正式地替我們做了介紹。那天道臨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列寧裝,看起來書生氣十足。房間很小,放了四張凳子便已轉不開身,道臨讓我們先坐,自己則站在我身後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識,很快三個“媒人”就聊得熱火朝天,我本來就內向少言,意外的是,道臨也很少插話,在我印象中,電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躍,能說會道,身後的這位似乎是個例外。
從招待所出來,道臨送我回家,我們沿著淮海路慢慢地走著。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過你演的《梁祝》和《西廂記》……”我並不意外,《梁祝》和《西廂記》是我們當年參加總政時回上海演的,想必是黃宗江請他去看了。交流藝術是最好的開場白,能讓我們彼此都不覺得拘謹,我隨口問:“哦,你覺得戲怎麼樣?給我們提提意見。”他倒也不客氣,馬上滔滔不絕:“我覺得祝英臺這個人物不同於一般的古代女性,她敢於女扮男裝去求學,並且追求自主的愛情婚姻,這種想法和行為即便今天看來,都是非常勇敢的。你的祝英臺,活潑熱烈的感情,我覺得表現得還不夠,表演上不夠放得開。另外,化蝶的舞蹈身段設計得有些簡單,中國的《梁祝》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都是雙雙殉情的悲劇結尾,藝術表現卻不一樣,前者寫意,後者寫實,這其實是體現了東西方審美觀念上的差異……”
一席話讓我有些吃驚,當時距離那次演出已經五年多了,我自己都有些印象模糊,他居然能記得那麼清楚,他對祝英臺的分析,完全符合我心中的設想,而提出的意見,也正是我一直覺得不夠滿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眼前的這位居然沒有絲毫客套,開門見山有話直說,倒讓我覺得他十分坦率誠懇,沒有那些讓人厭煩的圓滑世故。
“其實,我第一次遇見你,還要更早,是在卡爾登……”這下我愣住了,他笑著解釋說:“那時,我演下午場話劇,你們演夜場,我在後臺就看見過你。”接著,他又談了對《追魚》和剛上演不久的《紅樓夢》的觀感,我越聽越覺得驚訝,沒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課,有備而來,更沒想到他對藝術對錶演的見解,常常與我心中想的不謀而合。我停下了腳步,認真看著眼前這個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覺得好像重新認識了他,這種異常熟悉的感覺,莫非就是平時所唱的“眼前分明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那次見面以後,道臨開始給我寫信,道臨的信寫得多而勤,常常是我的回信還沒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書信來往如此頻繁,母親很快看出了端倪。母親喜歡看道臨主演的《渡江偵察記》,心裡先默默相中了這個“未來女婿”。當時,我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觀眾來信,都由母親先看,所有被認為有求愛嫌疑的來信,母親統統扣了下來,但凡是落款上寫著“孫”的,母親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裡。
(有刪節)
本文來自【嘉興日報-嘉興線上】,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