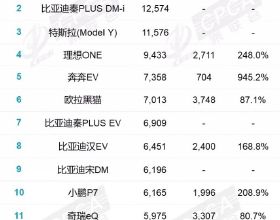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紅一方面軍西撤出發時有32名女性,幾天後兩位因病重新回到中央蘇區,走完長征全程為27名。
1、長征中的女性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撤離蘇區中央根據地時,在中央紅軍及後方機關共8萬餘人的長征隊伍中,有32名女性。出發不久,因工作需要,彭儒和陳璧英留下,未參加長征。正式參加長征的女幹部是30人(另有若干負責護理的婦女群眾)。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30名女同志隨軍參加,她們是:
王泉媛(在遵義嫁給王首道)、鄧六金(曾山妻子)、鄧穎超(周恩來妻子)、甘棠、危秀英(鍾赤兵妻子)、危拱之(葉劍英妻子)、劉英(張聞天妻子)、劉彩香(長征中嫁給畢佔雲)、劉群先(博古妻子)、楊厚珍(羅炳輝妻子)、李堅真(鄧振詢妻子)、李伯釗(楊尚昆妻子)、李建華(嶽夏妻子)、李桂英、吳仲廉(曾日三妻子)、吳富蓮、邱一涵(袁國平妻子)、陳慧清(鄧髮妻子)、金維映(李維漢妻子)、周越華(賀誠妻子)、鍾月林(宋任窮妻子)、賀子珍(毛澤東妻子)、錢希均(毛澤民妻子)、蕭月華(李德妻子)、康克清(朱德妻子)、曾玉(周子昆妻子)、謝飛(劉少奇妻子)、謝小梅(羅明妻子)、蔡暢(李富春妻子)、廖似光(凱豐妻子)。
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3人,1935年3月隨紅軍到達雲貴川邊時,因奉命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或另有任務而脫離長征隊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7人,於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動或被留在紅四方面軍。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後,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3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作戰。
王泉媛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死裡逃生,後來輾轉流離而淪落為民;吳富蓮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後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曾在西路軍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當幹部,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押至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於10月初回到延安。
因此,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於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後到達陝北者為24名。
參加長征的女性經過嚴格挑選:
一、共產黨員,政治思想好;二、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三、身體好,能扛東西會走路,體重差一點都不行。
一百多位女紅軍參加體檢(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只有二十多人合格。連董必武妻子陳碧英也被刷下來——體重差一斤。“免檢”的只有在中央機關和軍隊中工作的少數幾位大姐。
走出江西后,婦女分散各部諸多不便,於是就單獨成立婦女隊,劉群先任隊長,李伯釗任政治部主任。一個月後,黎平整編,婦女隊解散。
1935年隨紅軍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向雲貴方向突圍,開始長征的約有20位女性,其中有指揮員、機要員、護理員、炊事員,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有8000餘名女戰士隨軍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征。她們中有婦女獨立團(最多時達2000人)和500人的婦女工兵營(林月琴任營長),除負擔全營的生活物資外,還運輸供給部的財物,每人身上負重在四五十斤。此外,女戰士主要分佈於供給部、醫院、劇團及各軍洗衣隊,承擔著修路架橋、運輸籌糧、護理傷員、宣傳演劇方面的工作。
紅四方面軍的女戰士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屢經磨難,不少人二過草地,三過雪山。當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後,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的1300餘名女戰士組成婦女先鋒團(轄3個營9個連),參加西路軍的遠征。因敵我懸殊,轉戰途中女戰士傷亡慘重。到1937年3月在西路軍餘部中僅有的300名女戰士被編為婦女團,承擔掩護主力突圍的重任,最後大多數人被俘後轉賣或入獄,僥倖逃脫者則流落各地。
1934年11月,參加紅二十五軍長征的有7名女護士,並勝利到達陝北。
1930年代,在各游擊區堅持武裝鬥爭的女戰士同樣如此。她們主要有1930年中共瓊崖特委和瓊崖紅軍第二獨立師紅三團下屬的女子軍特務連(轄3個排)約120人經兩年的殘酷戰爭,女子軍因大部分戰士犧牲而解體。在1937年編入新四軍的原紅軍和南方各根據地游擊隊中,女戰士主要有皖西根據地一支三四十人組成的婦女排,閩贛邊界的汀瑞游擊隊也有20餘名女戰士等。1935年由原東北人民軍和抗日遊擊隊擴充套件建立的抗日聯軍7個軍,到1936年6月,其第三、四、五、七軍都有婦女團,最多時有300餘人。截至1937年夏,抗日聯軍45000名將士中,有女戰士688人。
她們奉獻自己的青春、健康甚至生命,參與了建立革命武裝的奠基。從人數上看,當時的女性在總人數中微乎其微,但她們已是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姐”這一親切的稱呼,是與“首長”、“戰友”一樣流行於革命隊伍中的尊稱,既有崇敬,又有患難友情。大浪淘沙,長征錘鍊了新一代中共的領導人,也形成一些享有極高威望的婦女領袖,如延安時期的四位大姐: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帥孟奇。
2、長征中她們有多難?
除康克清、蔡暢等少數幾位軍委直屬單位工作者,多數集中到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婦女隊,由何長工兼任連長,婦女隊長董必武、副隊長徐特立。董必武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德高望重,在女同志中很有威信。
婦女隊可不僅僅行軍,一路得“承運”六十副擔架。“鬍子隊長”董必武前後往返照應隊伍,既要鼓勵也要換肩,經常摔在泥坑裡,惹出“泥人董”的笑話。六十副擔架並不是空的,而是躺著傷病員,每一副都有4~6人抬換,每一位女兵得找到足夠的民夫,一路還得做民夫與傷員的思想工作,宿營時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董必武憶述:
初出發時差不多有六十副擔架,途中一個人要管理三四副,這是異常艱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軍,又不準點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擔架根本走不動。民工的步伐是不會整齊的。體力也不一樣。沒有抬慣,前後兩人換肩走路都不合拍,對革命的認識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路上臨時請來的,照料擔架的女同志跟著擔架走,跟得著前面的一副,又怕後面的掉隊,跟著後面一副,前面又沒有人照管。休息時候要防著民工開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兒,她們都不敢眨眼。特別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時候,民工的身體疲乏了總想打個瞌睡,宿營地還隔若干裡,前後隊全都催趕快走。這時,她們就在幾副擔架的前後跑,督促和安慰、勸說和鼓勵,用一切法子來推動民工往前走。有幾次民工把擔架從肩上放下來,躺在地上不動,無論如何都不肯走,她們中體力強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擔肩……
一次身高僅一米四十餘的“矮子”危秀英負責的兩副擔架掉隊了。她趕緊返回去尋找,找到後再追隊伍。此時,國軍飛機空襲,民夫沒見過飛機,撂下擔架就跑,一下跑掉三,剩下那個也不肯走了。擔架上是鄧發的妻子陳慧清,剛生孩子,根本無法行走,危秀英將陳慧清背到隱蔽處。再安置好另一名傷員,取下自己的半袋乾糧給那個民夫,讓他一邊吃一邊聽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
她從自己童養媳身世說到紅軍宗旨、眼下困難,民夫聽後不但自己不跑,還叫回兩位民夫。加上危秀英,兩副擔架終於啟程,翻過兩座山追上隊伍。危秀英在長征中還援助過後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廖志高。
另有資料記載:
紅一方面軍出發時還有一些女紅軍(可能中央縱隊之外),1935年6月15日,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紅一方面軍部隊半年多沒見女兵,有個戰士回憶道:
今天見到,十分高興!我想起從中央蘇區出征到湘江以前,我們一方面軍男女小紅軍很多,一路上許多人掉隊或犧牲了,尤其是女戰士,沒剩下幾個了,心裡實在難過。
紅四方面軍有婦女獨立團,團長張琴秋(1904~1968),全盛期擴為婦女獨立師。兩千餘二十歲左右的女兵,體格健壯,不蓄頭髮,全身戎裝,草鞋綁帶,做事如男兵。長征中,紅四方面軍婦女工兵營搞運輸、扛糧食、負彈藥、背大洋黃金。工兵營基本為川籍女兵身體結實,有力氣、能吃苦、負重百十斤爬山越嶺,日行百里,還要打仗。
1936年春,紅四方面軍快到甘孜,張國燾貼身交通隊幾個人,夥同幾個傷兵夜闖婦女工兵營駐地耍流氓。營長林月琴(1914~2003,後嫁給羅榮桓)下令還擊,傷兵的柺杖、工兵營運送的物資都成了武器,耍流氓的幾個人被女兵打跑,他們的幾支槍也被女兵繳獲。張國燾知悉後大發雷霆,反而撤了林月琴的營長。
3、作為母親那份難以割捨而又不得不捨的親情
1936年春,劉伯承三過草地時,鍾情於紅四方面軍女戰士汪榮華,開啟這位少女的心扉。1936年中秋節在甘南曲子鎮舉行簡單婚禮。張聞天也是在長征途中與劉英喜結連理。劉英時年三十,丈夫林尉犧牲於1928年春。
女紅軍的嬰孩只有兩條出路——送老家或送老鄉。送老家不方便,一般情況下只能由組織安排送老鄉。1929年5月,紅軍二打龍巖,賀子珍第一次分娩,產下一女,二十天送了老鄉,1932年4月第三次打龍巖,得知孩子已夭折。
1932年,賀子珍再生一子,長征前託給妹妹賀怡、毛澤覃夫婦。毛澤覃後將其轉移別處,毛澤覃犧牲後,這個孩子從此下落不明。1934年紅二方面軍長征途中,政治保衛局的戚元德在農民家生一男孩。
她取出身上所有錢及一件乾淨內衣,囑咐女房東:
“同志嫂!我把這個娃子連同這些東西送給你,娃子當做你的親生兒子算了!留下這件內衣作標記,將來我們的部隊回來,我一定來看望你們。”
女房東熬了半砂鍋米粥,勸戚元德休息幾天。戚喝了半碗稀粥,摸黑與兩位陪來的戰士跟上部隊。第二天凌晨,領導得知她棄子,派專人慰問。送來慰問品——半小碗鹽、一碗黑豆。
長征途中,賀子珍產下一女,因無法照料,只能選擇把女孩送給老鄉;西路軍時期,張琴秋因追兵在後沒辦法只能選擇棄子。
張琴秋是川陝紅區“女共黨”,全川聞名。1936年“九·一八”成都街頭剿共宣傳畫,她與徐向前被國民黨反動派居然畫成紅髮綠睛,手裡拿著小孩往嘴裡塞,甚至被說成每天要吃一個小孩,不吃就沒法活。由此可見國民黨反動派可恥的嘴臉。
張琴秋命運多舛,1924年4月入團、11月入黨;1925年11月在上海嫁沈澤民(茅盾胞弟,1933年病死鄂豫皖),夫婦隨即留蘇中山大學。1930年將新生女瑪姬安頓國際兒童院回國,1931年夫婦同入鄂豫皖;1936年7月三過草地前嫁陳昌浩,1939年8月27日陳昌浩隨周恩來飛蘇聯養病,因蘇德戰爭無法回國;1943年春,在陝北再嫁老戰友蘇井觀(1964年病逝)。1949年後,張琴秋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紅四方面軍一位女軍醫,隨紅二方面軍渡過噶曲河,三天後分娩,一副擔架抬母子倆。第二天夜裡,女軍醫還是擔心孩子成為部隊累贅,偷偷將嬰兒投入水塘。知道此事的人,幾十年都不願提起。廖承志在延安想以此為素材作畫,畫了幾十年都畫不成,一觸及“扔孩子”,手就顫抖起來。
1941年東北抗聯第六軍政委李兆麟,為了部隊安全,也扔過自己的新生兒,其妻不敢撿回,一位老友偷偷抱回。
隨紅一方面軍走完長征全程的三十位女性,四位在途中分娩,產後一晚或半日就要行動。一位分娩於藏區下打鼓,連青稞麥都吃不上,偶爾能分到一點羊肉,產後幾天便過草地。紅二方面軍李貞(1907~1990),過草地時分娩一早產兒(七個月),孩子餓哭不止,沒出草地就夭折了。李貞亦因產後沒休息,加上傷寒,永遠失去生育能力。
4、為革命工作不得不割捨作為女人愛美的一面
劉英記述長征中懷孕女性的有多難:
婚後懷孕,對於女同志來說,簡直是一種災難。孩子生下來,又沒法帶,對於做母親的感情上無異是一種酷刑,我看多了。賀子珍懷了孩子,誰也沒告訴,跟著隊伍走,在長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扔在在老鄉家裡,廖姒光(凱豐愛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扔下。這些孩子後來沒有一個找到的。劉群先(博古愛人)說得很俏皮:“行軍中騾馬比老公好!”這句笑話,說得很實在。
我認準了:在長征途中,要做工作就不能結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別想工作。我不能選擇後者。
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進入瓦窯堡,一直追求劉英的張聞天再次求婚:
“這下有了家,總可以了吧?”劉英此時才敢答應結婚,張聞天時為中共中央總負責。分給他們一孔土窯,沒有儀式,也沒請客。“情投意合,環境許可,兩個行李捲合在一起就是了。”
毛澤東來瓦窯堡後鬧過一次洞房。剛剛打勝直羅鎮一仗,毛主席興致很高,進門就嚷:
“你們要請客,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張聞天不會開玩笑,一到這種時刻頓時不知道說啥,劉英擋上前:“拿什麼請客呀?又沒有錢,又沒有東西!”
毛澤東笑道:
“那就不承認!我倒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還寫了一首打油詩呢!”
劉英記不得打油詩句,大意是誇讚張聞天講民主。
長征結束後,紅軍女性還有一則鮮為人知的細節:
剃光頭以滅蝨。所有長征女性都出現這種“革命蟲”。到達陝北後,身上的蟲子消滅了,頭髮裡的蝨子卻怎麼也搞不乾淨,又沒藥,賀子珍、劉英、劉群先等只好剃光頭。
1937年1月,劉英赴西安任青年工作巡視員,無法摘下帽子,因為頭髮還沒長出來。接觸青年只能由賈拓夫派一女同志,將西安學生領袖一個個領來接頭、交談。雖然入住西安六國飯店,也就幾間平房。李克農主管的內部招待所,吃到豬油熬白菜,就算美味了。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這一時期紅軍女性照片上都戴著帽子。當時的困難可想而知!
5、後來的她們
在抗戰時期,中共對婦女幹部的培養主要有兩個途徑:
(1)在各抗日根據地透過婦女救國會、婦女會等組織開辦短訓班,培訓從事農村婦女工作的女幹部。
據不完全統計,山東省在1938年夏到1940年8月間,共辦各級婦女幹部培訓班700期,受訓者達11600餘人;晉西根據地在1938年春到1939年春一年中舉辦婦訓班33次,受訓達62400人;晉綏邊區培養婦女幹部500餘人;晉東南中心區的遼縣開辦7期婦女幹部班,受訓近1000人。
(2)透過軍隊和根據地政府所辦的各類專門學校,有計劃地選拔女學員予以深造。
在延安,1937年底有一所八路軍抗日軍人家屬學校。該校專為工農出身的紅軍戰士及八路軍軍人家屬設立補習科、職業科,講授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從該校畢業的近300名學員,一部分進入延安其他專門學校深造。另外,在抗日軍政大學就讀的女生主要有:1938年11月總校第8大隊(女生大隊)654人,參加第四期學習;1940年抗大總校從延安遷至山西武鄉縣與抗大一分校合併,舉辦第六期學習班,有300餘女生接受培訓。
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中國女子大學,這是中共領導下的第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女大的辦學方針如毛澤東指出的:
“女大不僅要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幹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幹部。要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工廠去,組織二億三千五百萬婦女參加抗戰。”
據此,學生分別來自中央黨校、抗火,並由各根據地政府及地方黨組織選送。她們中既有經歷長征的女戰士,也有內地來的女青年。學校根據學員的不同特點組織教學活動,如高一班、高二班是一批經選拔品學兼優的學員,要被培養成有較高理論水平的婦女幹部;特別班是面向有工作經驗但文化較低的長征女幹部;陝甘寧班則專為陝甘寧邊區訓練基層婦女幹部而設。到1940年底,在校學員近1000人,共有14個班。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設有中央婦委書記。在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該職務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王明兼任的,蔡暢、鄧穎超、孟慶樹、劉英等為委員。隨後根據中央在各級黨的委員會下建立婦女部與婦女運動委員會。
另從零星的資料中也常會發現某些在各級黨組織中擔任要職的女性,1938年冬,擔任中共北平城委書記的是年僅23歲的女共產黨員周彬。1939年陳少敏擔任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政治委員,後歷任鄂豫邊區黨委書記、鄂豫皖區黨委副書記、鄂豫皖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等職。1945年11月,在東北剛解放的熱河重鎮赤峰市,新任市委副書記危拱之曾是一位長征女幹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陳修良。
在抗戰期間,中共卓有成效地將廣大婦女吸引到革命隊伍中發揮才幹,作出貢獻,婦女幹部陣容可觀。她們在軍隊中主要從事醫務、通訊、政治宣傳、後勤等工作。如1940年華南成立了抗日獨立總隊,其中有瓊崖女子軍特務連;1942年瓊總擴大為4000多人時,女戰士佔12%,1944年瓊總陣容達7000人時,女戰士比例上升為15%,她們幾乎承擔了部隊全部的炊事、衛生工作。
在解放戰爭中,華東野戰軍的女醫務人員佔全體前方醫務人員的30%;在東北野戰軍僅41軍就有女戰士398名,其中有被稱為“現代花木蘭”的特等女戰鬥英雄郭俊卿;在西北野戰軍中,隨軍的女醫務人員及宣傳隊員約200人。至於各地民兵武裝中的女戰士就無法統計了,在廣西解放前夕,據對陸川等39個縣的游擊區統計.有女戰士966人。
在瀏覽一份女紅軍63人(紅四方面軍僅列連級以上者)名單時注意到,她們中較為知名的有中共婦女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夫人,而大部分女戰士的革命生涯也許正是從長征開始的。她們擁有一段從女戰士到女幹部的非凡的經歷,這是她們值得驕傲的財富,但是女性要在人生旅途中掌握自己的命運有所成就,需要勇氣、毅力和進取心。這是一個漫長的奮鬥,對近代中國的女性來說,也許需要幾代人鍥而不捨的努力。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