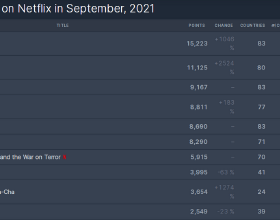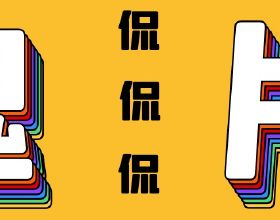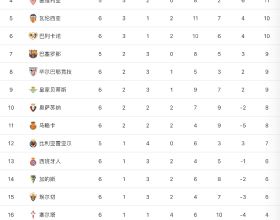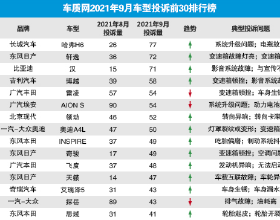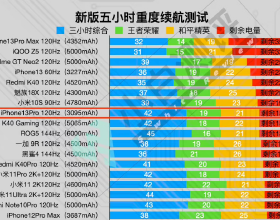於魁智、王蓉蓉、杜鎮傑、朱強、李軍、楊赤、宋小川……這幾個名字,在當代京劇舞臺上的分量不容忽視,他們是各個流派行當的翹楚,他們都屬牛,今年都60歲。今年6月,長安大戲院為他們舉辦了兩場名為“甲子之約”的專場演唱會,一票難求,盛況空前。
見證了新中國戲曲教育的變革,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戲曲藝術的低迷,而今又與日漸好轉的傳統文化一同攀向高峰。這批京劇藝術家站在人生的甲子時刻,回望從藝道路的點點滴滴,他們明白,所有的好與不好都成就了今日他們的財富。
學員隊歲月(第一排右一為於魁智,第二排右二為朱強)
甲子之約
見過“真神”,成為得天獨厚的一代
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他們,經歷過共和國艱苦的時候,但京劇巔峰時刻的餘暉也曾照拂過他們,用梨園行的話說就是“見過真神”。
朱強、於魁智都是瀋陽人,1972年一起考入瀋陽京劇院學員隊。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地方的藝術資源有限,想要遇上名師太難。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許多京劇大碼頭的名家被下放到各地,在瀋陽也有不少這樣的大家,當初瀋陽京劇團學員隊的老師就有尹月樵、黃雲鵬、姚世茹、焦麟昆、秦友梅等人。經歷了舊時代的老師們,不能演戲了就把熱情投諸教學,傳統戲不能唱了,但傳統的戲曲教學方式還在繼續。朱強回憶說,那時候覺得老師太嚴厲了,學習過程非常辛苦,“每天早晨五點多起床練晨功,晚上還要練夜功,老師不用說話,一瞪眼你就害怕。”朱強有一次胳膊骨折住了二十多天醫院,出院就回了學員班,練功的時候想著胳膊就不用練了,跟著大家壓腿就行,誰知道老師卻說,左胳膊不行就用右胳膊練習“鐵門檻”,“在老師們看來,學戲哪有不受傷的,你就不能閒著。”今天看來,老師當初的嚴厲讓他們班的成材率非常高,同班三十多個演員學員中就湧現出了他和於魁智、李靜文、張宏偉、張微等諸多今天還活躍在舞臺上的角兒。
杜鎮傑是從山東農村走出來的演員,他在進入中國戲曲學院後,以及後來的工作中都與不少名家學習過,合作過。1979年,杜鎮傑高中文藝班畢業回到家中務農,後來聽說中國戲曲學院到濟南招插班生,沒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到了戲曲學院後,和其他從小學戲的同學相比,他基礎薄弱的毛病一下兒就暴露出來。在學校,那些比較優秀的學生都由正當盛年的老師來教,杜鎮傑他們比較薄弱的學生則主要由劉盛通、王世續、李世霖、李甫春、楊韻清、吳澤東等諸多從富連成等老戲班走出來的年紀比較大的老師來上課,也算是歪打正著遇上了“真神”。後來,他又在馬長禮先生的引領下,走遍北京城尋訪名師,先後跟隨李盛藻、關盛明、葉盛長、馬崇仁、遲金聲、譚元壽等名家學習,時至今日,杜鎮傑還經常去和九十多歲的遲金聲老師學戲。
大連京劇院院長楊赤則直言,沒有袁世海先生就沒有自己的今天。那時候,他在大連工作,袁世海先生在北京,師徒倆兩地奔波地教授、學習,“大連市的領導也非常重視年輕人的培養,為了方便袁世海先生來大連教學,專門給他安排了駐地。”
王蓉蓉進入中國戲曲學院後,得到張君秋大師的親授。王蓉蓉至今記得,有一次老師在排練場看了她演的《四郎探母》後,專門到學校給她說旗步的走法與別的腳步有什麼區別,劇中的請安動作應該怎麼做,“他當時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一遍又一遍地給我做示範,講要領,手放在什麼位置,腿是怎樣的蹲法,手帕是怎樣的拿法,不厭其煩。”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得天獨厚的。”楊赤說,一個演員最關鍵的是他的成長期和成名期能遇到好的機會和環境,而他們都遇上了,這個優勢是今天的年輕人沒有的。
跌落谷底,也堅信未來有希望
在開啟這個職業生涯的初期,這一代人並不知道在“得天獨厚”的後面還尾隨著“跌入谷底”的命運。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二三十歲的他們正是嶄露頭角的時候,但京劇卻遭遇低迷的時刻。王蓉蓉回憶說,那時候演出特別少,一個團一個月也就三四場演出,一個演員一個月能有一場演出就不錯了,有時候一個月都沒有一場演出,“有演出需要排練的時候就上半天班,不上班也沒人管,劇場也沒什麼觀眾,一場演出也就賣幾十張票,演員的待遇也低,一場就5塊錢、10塊錢。”同在北京京劇院的杜鎮傑也感受到了那種壓抑的氛圍,成天沒事兒幹,就在家裡睡覺。朱強說,演出少生活拮据,大家也都著急,劇院還真有同事去賣花。“大幕一拉開,臺上幾十個演員,臺下只有幾個觀眾。”楊赤說,經歷那樣的情景誰都會著急。
面對這樣的現實,很多人失望了乾脆轉行,出國的、下海的、拍電影的、唱歌的、演話劇的……而今天仍然活躍在舞臺上的他們,在那樣的時代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
“雖然劇院安排的工作少,但我每天給自己安排的日程還是滿滿的。”王蓉蓉說,那時候全靠自己管自己,幾個年輕人約著早晨一起去練晨功,在學校沒練的基本功,那段時間都補上了。下午的時間就自己聽錄音學戲學唱,整理唱詞、背戲。王蓉蓉說,那時候沒有什麼劇本,自己看戲的時候就找個沒人的角落坐著,開啟錄音機把老師們的演出錄下來,有的時候還要自己低聲把臺上的表演、排程說進去,回來再扒詞兒,整理劇本。“別看那時候沒事兒幹,可是我都沒有時間逛街,一天不練功學唱就覺得自己在虛度時光。”王蓉蓉說,正是因為平時有這樣的積累,關鍵的時候才能接下難啃的骨頭。有一次劇院臨時讓她替一個演員演四出大戲,雖然有的戲她沒演過,但平時已經學了,詞兒都能倒背如流,才敢接下來。
朱強也說,那段時間雖然過得有些煎熬,但他一點時間沒有浪費,一邊找老師學戲,一邊還自學,取得了大專文憑,“那時候學的戲,看的書,到現在都管用了。”
杜鎮傑的經歷則多了一番曲折。在最低谷的時候,他不想自己的大好時光就在矇頭睡覺中度過,他想走出去看看。1994年,他選擇了停薪留職,去了香港。也許有人覺得在京劇最艱難的時候,他做了“叛徒”,但杜鎮傑覺得,自己是農村出來的孩子,每一天的光陰都浪費不起。那時候做生意比唱戲掙錢多,頭腦靈活的他也跟著下海經商,而且生意做得風生水起。轉眼三年過去了,雖然錢掙了不少,但他始終無法割捨對舞臺的眷戀,生意場再風光,也無法替代他心中觀眾熱情的掌聲。1997年,他重新回到了劇院。“過去耽誤的時間得一點一點往回補”,他又開始像從前一樣每天練功,不斷學戲,堅持演出,雖然累出了一身毛病,但是他的心裡是踏實的,充實的,幸福的,因為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感恩時代,誓將“幸運”傳遞下去
他們自然也是幸運的一代,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國力越來越強,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京劇作為國粹受到更多關注,他們也得到更多機會。
1980年,恢復了傳統戲的演出,當時剛剛二十歲左右的王蓉蓉、李宏圖參加了第一部恢復演出的傳統戲《四郎探母》;王蓉蓉的學士學位證書是001號,她和她的同學們成為中國戲曲歷史上的第一批本科生;1996年,王蓉蓉又和楊赤、李軍、朱強等人一起進入第一屆中國京劇優秀青年演員研究生班(簡稱“青研班”),使他們在表演技能、文化水平、人文素養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提高。
楊赤則認為,這一代的幸運在於,即使處於低谷也能看到希望,有一個清晰可見的上升通道,“我們那時候有梅蘭芳金獎,有央視的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一旦獲獎了,全國人民都知道。我們中間很多人都是透過大賽成名的,所以你知道你經過努力能成為角兒,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讓他遺憾的是,這些大賽都取消了,今天的年輕人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也曾在自己的提案中建議恢復青年演員大賽,讓今天的年輕演員有個奔頭。
得到了這麼多機會的他們,也都願意為自己鍾愛的事業做更多,即使他們已經六十歲了。今年上半年,王蓉蓉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不再擔任北京京劇院一團團長。她說,這幾年她的主要精力還會在舞臺演出方面,過幾年就會逐漸往教學方面轉,“我有19個徒弟,以前都顧不上他們,今後也得管管了。”朱強則正在辦理退休手續,“我服老,但我還愛這個舞臺,有需要就還去演。”今年執導了京劇《嫦娥奔月》的他,還發現了新的興趣點,想要再嘗試一些導演的工作,把自己這麼多年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
這些年來,杜鎮傑一直致力於傳統戲的挖掘、整理、學習,“我已經演了七十多出戲了,可以自信地說目前還沒有人能演這麼多戲。”眼下他一邊忙著演出,一邊還在北京市政協做籌備“戲曲苑”的工作,將來要去做一些京劇藝術家和作品的搶救性工作,去做一些京劇的普及、推廣。
楊赤還沒有退休,他希望還能為京劇做更多的工作,在他看來,當前京劇事業中人才的培養是重中之重,他自己會拿出更多時間給年輕人上課。
記者手記
這是一次特殊的報道,我們希望透過對這幾位今年六十歲的京劇人的“速寫”,為一代京劇人畫像。
這一代人是京劇歷史上特殊的一代。他們的學習生涯被京劇巔峰的餘暉照拂,見過真神得到真傳,但也經歷了傳統戲不能演,只能學樣板戲的年代;在壯年時代又與傳統文化最為低迷的時代相遇;經歷大浪淘沙之後,他們的藝術生命在最好的年代迎來最高光時刻。觀察他們職業生涯,還會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終身學習。無論在京劇表演方面天賦如何,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境,他們都從未中斷學習。我們也希望透過對他們職業生涯的記錄,讓年輕的京劇人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充滿信心,經歷了那麼多坎坷的他們尚且能夠一顆初心到今天,在傳統藝術越來越受到重視,各方面條件都越來越好的當下,一定有更好的未來在前方,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努力?
文/北京晚報記者 牛春梅
編輯/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