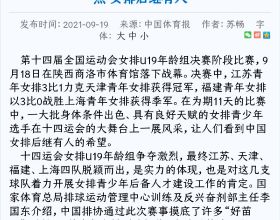我的書房,原來有陽光照進!
若不是一早要找本書,竟無從知曉書房裡有陽光可以照進來!這是我住了十多年的房,一直主觀認為,南北向的房子,我的安置在西南角的書房是照不見太陽的,以此從未有過哪個早晨,坐在書房裡看過幾頁書,也許是有過這麼一兩個早晨,也忘了吧。 朝陽穿窗而入,帶來異樣的神奇。 書櫃豎放的書籍 ,沐在陽光裡,這一大片亮汪汪的光,帶著清晨涼幽幽的空氣,投射在西牆那邊一排大書架上。光照的地方連書脊上的文字也看得異常分明。《亂世佳人》和《沉浮》緊靠在一起,書名是白色的,印顯在紅底的書脊上,格外顯眼,好像在驕傲地說:“那個戰爭年代勇敢的女人,和當代職場上拼搏的女人一樣美麗。”
正午一過,日頭偏西,陽光就照進我東西向做瑜伽的屋子。 此屋西南角,一個旋轉的書櫃,被陽光帶著窗外樹影透射進來,書櫃一片斑駁,將近六點,光線越來越弱,那一串從頂端垂下的綠蘿,隱在暗中,一束弱弱的光,滲透過窗紗,像是給綠蘿旁側的書籍鍍了一層金粉,此刻,我若要湊近去取一本書,那束光,恰好打照在我的嘴唇,似乎想撬開我的嘴巴,聽一聽我混跡於人間的感慨,可是,我只口含夕陽,閉嘴不言。 一隻雀,隱在窗外那棵香樟樹的枝葉間,啁啁唧唧,是準備在夕陽裡安歇了吧。我亦席地窩靠在牆邊,看夕陽最後拋給書籍的光芒,一點一點緩慢消褪。那排《蔣勳說紅樓》,剛才還明晰可見它書脊上的字,這會兒,全靜默在暗影裡。
最後一瞬,夕陽殘照已經挪到我書架最上邊的一格。滿室暗下來,只有書架這一格無限明媚。那裡斜放著胡塞尼的《燦爛千陽》,書的封面已泛黃,我似乎又見那個叫萊拉,美得驚人倔強的女子,將近十年過去了,但是,和塔裡克站在陽光之下,萊拉剎那之間覺得這些年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她父母的死亡,和希拉德的婚姻,殺戮,火箭彈,塔利班,捱打,飢餓,甚至她的兩個孩子,所有這些恍如一場大夢;這將近十年的光陰彷彿只是一條奇怪的時間岔道,隔開了最後想出的那個下午和充分的這一刻,或許是萊拉感動了夕陽,也或許是《燦爛千陽》應和了即將逝去的夕陽,一瞬間,高高立在書架上格的《燦爛千陽》,被最後的陽光輝映得奪目和通紅,好似燃燒了起來。
瞬間,一片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