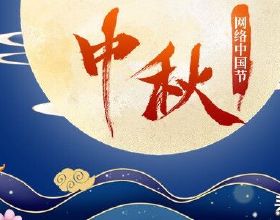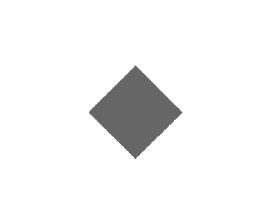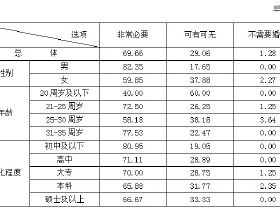當風安詳,樹溫順,靜謐寫滿乾坤,世間悠然端莊,落雪就有了悄然和隱匿性。軒窗的透明被室內外迥異的溫度塗抹出一層朦朧和模糊,安逸於暖氣屋的人們是難以瀏覽室外律動的風景的。這當兒,一俟有雪光臨,天地間會籠罩一片皚皚的白,倏然出屋,驚喜和祥瑞就會讓心境敞亮。世間萬物戴雪帽,千樹萬樹梨花開,雪景,讓大自然銀裝素裹。
夜間落雪是常態,更具幽然性,當疲憊的人們溫馨入夢,大地便招來天宮之客。紛紛揚揚,或零落稀疏,或濃密奔放,它彷彿接受了光的賦予,用通透的白,把黑夜暈染,黑白邂逅交織,大地便有了恍惚和微微的亮堂。
積蓄和等待頗具耐性,夢鄉里沿著漆黑的路徑一直走下去,到了盡頭就會迎來朦朧的黎明。天光點亮了東方,寂靜的晨就會緩緩騷動起來。
雪的無聲往往侷限於慵懶的酣睡者,其實靜態中降雪也是有語言的,這些無聲的語言,入耳無效,是入心的。纏絡於心境,與心呼應,別人難於感悟,聽不明白,除非是殷勤的鄉人。
雪舞乾坤,落雪無語,卻喚醒了勤奮者。力量,是心中沉默和潛伏的軍隊,翻身下炕,開啟房門,棉絮似的白,厚厚一層覆蓋院子。一會兒,耳畔便有了聽覺的盛宴,那些掃帚、鐵掀,掃雪、除雪的交響曲便叮叮噹噹演奏起來。各掃門前雪,門前、大街、衚衕,平坦的路面瞬間便坦露出來。街道上,著橘紅色服裝的街道美容師,習慣性為雪天增添風景,正逐條衚衕裝拉當日垃圾,開啟晨曦下的文明之美。
接下來,女人的戲演繹在廚房,煙火味飄逸開來,家人圍攏餐桌,為新的一天聚集能量。
孩子們有著和雪一樣的天真、喧騰、調皮、好奇。當溫馨又親切的母愛把他們從暖融的被窩裡拽出,魂兒便被窗外雪牽拉而去,哧溜逃離母親的關愛,光溜著身子,望著滿世界的白,心緒便狂舞起來,那些腦際間儲存的桀驁遊戲,又要付諸於行動,堆雪人、滾雪球、打雪仗,遊弋雪地,踏雪聽音,爛漫又愜意。
人生最大的快樂,就是簡潔和輕鬆,然而,快樂的音符往往倉促和短暫。
嘀嗒的時音規矩著孩子們天馬行空的思緒,該上學了。匆匆幾口菜飯之後,孩子便被棉絮簇擁起來,棉帽、棉鞋,棉手套、麵包服、鴨絨褲,還有身後馱著的一個沉甸甸的責任,儼然天外來客。跨上電動車後座,依附著爸爸的強健和偉岸,或者媽媽的馨香和浪漫,孩子的小手捕捉著偶爾降落的零散雪花,讓它瞬間溼潤,化作一縷望不見的暢想,細細收穫和儲存著孩提的逍遙和稚嫩天性。保持一顆童心,以詩心和童心打量世界,總是快活的、完美的、充滿蓬勃和幻想的。
路上散松的厚雪,在一番番的車輪和腳底壓迫下,變得結實和滑溜溜,許多父母的騎車技術經不住考驗,紛紛倒地,引來繁多的唏噓聲。倒地翻滾的孩子仍快活著,逗趣、頑皮、嬉戲不止。男人的罵聲、吼聲、吆喝聲,以及熟人相見的搭訕聲,孩子們的吵鬧聲,交織感應在茫茫雪地,為記憶的行囊平添內容。
雪落大地,曠野神秘而遼闊,不只是苟且在暖融的囊括,凜冽下的越冬作物與它的主人有著心靈的感應。融於雪叢的蒜苗、圓蔥苗彷彿凍僵,沒了生機,承受著一份無奈的蒼涼,它的根鬚卻如遊動的蚯蚓,在土壤中向著地心的方向漫溯,殷殷汲取著大地母親的溫暖。大片的麥苗,隱遁了綠色,覆蓋著白雪,卻做著無憂無慮的夢幻,隱隱有一種家園的親切。站在田野的邊沿,舉目遠眺,恍惚間,農人的視野裡躍動著黃燦燦的六月,烈日當空,大蒜出土,圓蔥膨脹,機聲隆隆下,麥粒歸還入倉,齊刷刷的麥茬佈滿大地,陽光下熠熠生輝。他們還會看得更遠,期待愈加豐腴的福祉寫滿家鄉。
雪花是冬天的怒放,化雪是生命的點綴,一切都是自然又美好的事情。冬天不見雪,就像畫龍不點睛,栽花無豔美。有了雪的參與,冬季便繁華起來,人變得通透舒坦,妙筆丹青刻畫出“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氣魄和雄渾磅礴,也呈現著描摹潔美和多姿,給人歡欣和幸福。成全了抬頭有盛景,富庶在醞釀,來年有花開,福瑞翩翩來的意蘊。
天寒地凍,你是否覺著,人至優雅處,乾坤間宛若躍動出一種瑞喜,春芽般拱破了冬的封鎖,將一顆又一顆的素心,染得融融的暖。